关于如何做好煤矿安全培训的探讨
2014年5月08日 16:25 作者:王 伟王 伟
(神东煤炭集团哈拉沟煤矿 陕西 榆林 719315)
[摘 要]安全工作是煤矿生产中的头等大事,研究表明,我国企业工伤事故产生的原因50% ~ 80%与不安全行为有关,因此做好安全培训对于保证煤矿安全生产具有重要的意义。文章分析了目前我国煤矿安全培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几条做好煤矿安全培训的措施。
[关键词]煤矿安全;培训;培训计划;培训方式
中图分类号:TD7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17-0316-01
图1 煤矿企业安全培训模式图
一、多维社会主体对环境侵权诉讼的法治期待
关涉环境侵权的现实诉求,是一个国家发展过程中必须客观面对的迫切问题。自然环境一旦受到破坏,其是极不容易得到恢复的,并且环境侵权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地刺激着政府与社会的理性神经,因而多维的社会主体在这一问题上较为一致的把视线投向司法救济的权威性选择。
环境侵权的现实力量对比诠释出弱者之音与强者之力的本真图景,期待司法救济成为其实现正义的必然诉求。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差别巨大的空间,尤其是按照这个空间所提供的稳定的且能够支持或满足稳定期待的机遇的程度不同,差别也不同。”[1]在具体的环境侵权案件中出现的各方主体在社会现实情境中,其往往展现出的是一幅较为悬殊力量博弈的情景画,如云南的洱海污染事件、淮河污染事件等等。司法是实现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这似乎成为司法救济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我们可以这样判断,对环境造成的危害越大往往是双方力量对比最为悬殊的具体大案,其对司法所抱有的期待就越具有典型性,司法系统的功能彰显也就成为司法能动的主要动因所在。学界在探讨环境侵权属于民事法律与行政法律救济的属性之争之时,公益诉讼成为诉讼法学界的热门话题。哈贝马斯强调,“经过专业证明的标准要确保的是判决的客观性和对它进行主体间审查的可能性。”[2]而一个个个案给我们表征出的环境侵权造成的各种具体危害是多么令人触目惊心,而最终的救济效果却又是如此的微弱,这些现实情景让受害者对各种救济手段所抱有的各种信念只会是渐渐消散。我们认为,环境侵权的现实救济逻辑已经将思维路向转入积极寻求司法救济的社会理性决定中来,已然达致社会多维主体的一般性共识,不论其效果如何,已然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救济手段,是寻求社会正义的实然性选择判断。
二、环境侵权诉讼案件的差异化区分
波普尔指出,“内容和实际解释能力对于理论的先验评价是最重要的调节性概念。它们与理论的可检验程度密切相关。”[3]学界较多的把注意力投向司法救济的案件属性的判断上,即环境的宪法基本权利与一般民事权利,而司法实践基本上是将该类案件确定在民事侵权诉讼中予以解决。首先,从环境侵权的侵害主体上,可以分为个人、企业与政府三种类型的环境侵权诉讼。关涉环境侵权的侵害主体的研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似乎对环境侵权的实际损害的关注中无需对是由谁造成的没有太大关系。不可否认的是,环境侵权事实一旦成为现实,其给社会所带来的危害确实令人触目惊心,而司法救济是需要危害事实发生以后才会得以展开。在环境侵权的现实案件中,进行侵害主体的类型识别可以较为明晰地确定侵害主体承担责任能力的基本判断。
其次,从环境侵权的诉讼属性上,可以分为民事、行政与刑事三种类型的环境侵权诉讼。环境侵权在具体的案件类型上似乎无需进行关切,因为诉讼属性的区分需要在相关证据得到有关主体认定以后自然成为确证其类型的具体判断。正如“给与个人对权利主张以最大范围的欲求,也许必须同要求公益的论点进行平衡。”[4]司法救济在具体的案件中对于受侵害的当事人而言具有较大的难度,选择何种诉讼类型进行权利救济往往不是完全由其来决定的。诉讼类型的三种属性在法律要件上具有较大的差异,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对于受侵害者而言具有较大的选择性,也就是说可选择也可以不选择进行司法救济,或者选择何种形式进行救济,而刑事诉讼则是由检察机关来行使的。对三种诉讼类型在环境侵权的具体案件中进行识别是一个极为有效地逻辑路向,因为环境侵权诉讼的特殊性在于其对社会的破坏是一个国家发展阶段的突出问题,科学发展观在诉讼类型上需要得到较为具体的体现,就唯有分出差异化处理的司法救济类型才是真正解决环境侵权危害的理性选择。
三、环境侵权诉讼中司法独立性品格的形态表征
正如沃尔夫所指出的,“法官们会注意公众对他们判决的批评这个事实也可能使他们有动力写出理性的好意见,但是这也会使他们只一味迎合法律界的意识形态。”[5]在法治精神得到高扬的时代中,对司法权的期待成为司法系统积极能动司法的源源动力,但是需要进行理性考量的是司法功能限度,应在司法法治逻辑中应该遵循的规制建构主义路向。
第一,立法的普遍性缺位是环境侵权诉讼无法达致司法救济应有效果的关键要素,国家权力的制度配置成为司法功能限度的应然要求。在司法现实中,环境侵权诉讼的各种具体案件往往在寻求原告资格上经常发生颇为尴尬的情形,即侵害事实极为鲜明,却因为环境的公共性特征使得谁成为原告却颇为困难。出现此种情形绝不是单一个案的孤立事件,而是困扰司法救济的制度瓶颈。第二,政府责任在环境侵权案件中缺乏明确指向性,极为现实地考验着司法独立性品格的坚守。
第三,企业责任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缺乏制约机制,环境侵权的损害赔偿数额拷问着司法判决的权威性与实效性。在面向一个个环境侵权案件时,我们似乎不该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企业责任的承担往往与其获得的利益相比是微乎其微的,也就是大家熟悉的道理:违法成本太低,使得其对环境侵权不惧诉讼的内在原因。
第四,司法系统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相关技术性知识陌生,相关环境侵权损害认定能力不足阈限着其功能价值的发挥。对环境侵权诉讼中司法功能限度的考量,我们发现,司法救济并不是解决环境侵权的最佳选项与寄托所在,司法能动的积极性值得警惕,否则司法法治的规制路向就会成为司法权威性获得的空谈与妄想。当然,对司法功能限度的追问并不评判司法系统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应有的功能价值彰显,而是需要在理性建构主义的路向上为环境侵权诉讼探寻法治力量的真正施展平台。
四、环境侵权诉讼的司法应对机制
司法系统权威性与实效性具有较大的相关性,尤其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对违法者予以严惩和相关受损方予以救济,是司法彰显功能价值的国家权力结构安排所在。保罗?利科认为,“统治要求有一种约束性策略;而不协调则要求具有证成策略,由一系列论证构成并旨在于争论和诉讼中有效。”[6]因而,环境侵权诉讼应在理性建构主义的路向上探寻司法应对机制。首先,司法系统应正确识别自身功能限度的范围,区分环境侵权诉讼的司法救济的社会期待与诉讼类型差异。其次,司法系统应遵循司法法治的规制路向,在环境侵权诉讼中不求案件多少,而力争案件质量上得到应有的社会效果。最后,司法系统应积极寻求立法的支持为环境侵权诉讼探明终极关怀的制度依据,尤其是在处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对行政机关的建议性主张。环境侵权的相关立法位阶的问题一直是学界认为解决我国当前环境侵权不利的主要原因,而如何解决立法不足的问题确实值得进行较为广泛的讨论,但是,司法系统在此方面应有较大的发言资格,相关案件的具体数据是说明立法考虑不当的有力明证。总之,面向社会期待的环境侵权诉讼,司法系统需要在严格遵循法治规制路向上保持应有的理性,客观判断司法功能限度,在终极关怀中寻求解决环境侵权的建构主义路径该当成为其职责与使命。
作者简介
张翠萍,女, 现任国投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法律顾问室主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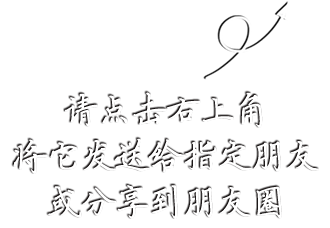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