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雨王汉德森》与贝娄的犹太文化意识
2011年4月18日 17:16 作者:论文网《雨王汉德森》在索尔贝娄(1915—2005)整个文学创作过程中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它在许多方面与贝娄其他作品截然不同,学者们直到今天仍很难确定它的文类属性,人们对它的解读模式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在这部小说中,贝娄创造了其作品里唯一的非犹太主人公形象——尤金·汉德森,一个五十五岁的美国白人富翁,而贝娄却认为自己与这个人物最为相似。贝娄的主要小说大多以纽约和芝加哥为背景,但他为这部小说选择了辽阔旷远的非洲作为主体故事发生的布景,而在小说出版之前他甚至根本就没踏上过非洲这片土地,单凭个人想象杜撰了两个处于原始状态的非洲土著部落,这种做法甚至惹恼了他大学时代的人类学导师。虽然贝娄一再警告读者不要试图在他的作品中费力地找寻象征意义,但《雨王汉德森》可以说是贝娄全部小说中象征色彩最为浓重的。然而仔细阅读这部作品,读者不难接受这样的判断:这部小说与贝娄其他小说的关系最好定调为貌不合而神不离。贝娄是位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其作品的基调就是对人生意义、人性本质、人类社会价值体系、道德观念等重大问题的探索,《雨王汉德森》也不例外。美国一位早期贝娄评论家就认为它最能反映美国20世纪50年代丰裕社会的基本特征——“异化、价值观的沦丧、宗教信仰的消解和文化的缺失”,而汉德森正是这种社会的典型产物,只是社会尚未能将他彻底异化,他骨子里不断渴望对更高精神品质的追求和生命本真的还原,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娄说《雨王汉德森》是他的宠儿。虽说作品本身可能比作家本人的声明更可靠,可贝娄对《雨王汉德森》的偏爱也不是没有道理:无论从艺术手法还是主题设计上来看,这部小说都具有典型的贝娄风格,比如其超乎寻常的喜剧色彩、关乎人生真谛的形而上学思辩、雅言与俗语交织成趣的文风及主人公展示出的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的精神,但尤为重要且常为渎者所忽略的一点是:贝娄这唯一一部以非犹太人为主角的长篇小说,在许多方面却更能说明犹太文化意识对作者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
“文化”一词可能是当今批评话语中滥用程度最高的,有些批评家认为“文化”一词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明确的含义了。早在1952年,两位著名人类学家AlfredL.Kroeber和ClydeKluck—hohn就对“文化”的定义做出了160种区分,犹太文化更是历经数千年的发展与变迁并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中,连“犹太”这两个字的意义现在也变得模糊不清了,但这些都不是本文试图理清的概念。任何形式的研究总要借用一些通用说法并对它们的含义作出必要限定,Ray—mondWilliams用“文化”一词来指称所有智识、精神和美感发展的普遍过程。贝娄是一位生长于一个说意第绪语的东欧犹太移民家庭的作家,所以本文用“犹太文化意识”来指称其文学创作的主体背景。虽然贝娄本人对评论界乱贴标签的做法十分反感,他甚至反对别人称他为美国犹太小说家,但正如ElieWiesel所说的那样,“无论是情愿还是不情愿,犹太作家就是犹太人,不可能是别的什么。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对自身犹太性的拒绝也足以表明他的身份”。本文拟从三个方面对贝娄的犹太文化意识和《雨王汉德森》创作的关系进行简要分析,以期为读者解读这部作品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丰裕社会的典型,在普通人眼里,汉德森是这个社会的宠儿:出身豪门,曾祖父做过国务卿,长辈亲属中有几个当过驻英和驻法大使,父亲是著名学者,好友圈中包括威廉·詹姆斯和亨利·亚当斯;汉德森本人则从小养尊处优,受过良好的教育,常春藤联盟校硕士毕业;由于哥哥早逝,他独自继承了汉氏家族的三百万元遗产。但他却是贝娄笔下最疯颠、最粗劣无礼的一个怪物:在祖传的别墅里养猪,莫名其妙地向人挑衅打架,整天烂醉如泥,在亲朋好友面前装疯卖傻。那么,读者该如何解读他这些古怪的行为?对现实社会的严厉批评是美国犹太作家创作的典型特征之一。虽然贝娄一贯反对有人给他贴上“犹太作家”这样的标签,但犹太文化意识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雨王汉德森》这部小说前四章对主人公的刻画及对其生存状态的描绘正是作者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现实社会的讽刺和批判:“这地方遭到了天罚。事情搞得一塌糊涂。出了什么毛病啦。这地方遭到了天罚!”汉德森物质丰富、生活优裕,但他却显得和这样的生活背景格格不入,像一个流浪在荒原里的幽灵,空虚、孤独、压抑、迷茫,内心充满了恐惧,“在这无边的冷漠中,我感到就要死了。”他想在书中找寻生命的真理,可在那里找到的却是他父亲夹在书中做书签的一张张钞票;为排遣他那空洞寂寞、百无聊赖的日子,汉德森酗酒、打架、养猪、胡闹,但不管他怎么样,整个世界依然从四面八方压得他无法喘息,内心深处总有一个“我要,我要!”的声音把他搞得心烦意乱。但究竟要什么?他总是弄不清楚。他用自杀来威胁他的妻子莉莉,让她停止说教,因为他知道莉莉的父亲是在家里一场争吵之后开枪打碎了自己的脑袋;他把漂亮的农舍、草地、花园都变成了猪圈,整个地方搞得臭气熏天因为他认定自己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猪圈。物质的丰富、科技的进步却反而加重了人类感受能力的退化,汉德森的烦恼正源自他对这种状态的抵制,他家的女佣伦诺克斯小姐之死第一次让他对自己及现代人生存的真实状态有了实在的感悟:“可耻啊,可耻!真是大大的可耻!我们怎么能这样干呢?为什么容许自己这样干呢?我们在干什么名堂啊?最后那间小泥屋在等待着你,连扇窗都没有。所以,看在上帝的面上,汉德森,采取行动,做出努力吧。你也会死于这种瘟病的。死亡会消灭你。除了一堆垃圾,什么也不会留下来。”借汉德森之口,贝娄在这里表达了他对20世纪50年代美国所谓富裕社会的强烈不满,工业的进步、物质的丰富只不过就是满足了人类的生物性需求,技术进步与物质主义的胜利并不能掩盖现代人生活的空虚和精神的涣散,整个社会生活仿佛患上了瘟疫。贝娄这种社会批判精神在后来的作品如《赛姆勒先生的行星》《更多的人死于心碎》中表现得更为激烈。 省级论文发表对于作家所肩负的特殊使命,贝娄作过这样的阐释:“在这个由各种各样物体所构成的物质世界里,几乎所有人都被教导把自己也看作某种物件。那么劝导人们把自己视为一个真正的主体实在是件值当的事,而不是让他们把自己当成某种值98美分的矿物质然后永远消失在1500美元的棺材里。”在汉德森这一人物身上,读者能清晰地看到一个渴望洗心革面的现代人形象,他拒绝把自己看作一个无生命的物件或某种价值98美分的矿物质,他更像早期的浪漫主义诗人,拒绝一切对生命和人性的虚无主义论调,坚信现代世界的喧嚣不能抹杀人类心灵的存在,尽管这个世界把他压迫得快要窒息了,他的所有古怪的行为恰恰表明了他对这个阻止“人类情感想象和灵魂渴望”的世界的愤怒和对以二战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所谓“丰裕社会”的批判。
单纯对现实世界的批判自然不足以成就一个伟大的作家或一部优秀的作品,犹太文化最令人敬佩的一个本质就是对人道主义的信仰,对人性和未来总是抱有乐观主义的信念,这也许是支撑犹太民族历经两千多年饱受迫害的流散生存状态却依然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石之一。而贝娄全部创作的基调正是在批判否定背后潜藏的对人性和未来的肯定,他坚决摒弃以某些现代派作家为代表的现代荒原意识和虚无主义哲学。汉德森正是这样一个“高尚品质的可笑的寻觅者”,一个拒绝接受自己和世人生物性存在的勇士,一个固执地挖掘世界与人性珍宝的人,不管自己的努力在现实的世界里显得如何荒谬与可笑。在诺贝尔奖受奖演说中,贝娄引用康拉德的话说:“艺术试图在这个世界里,在事物中以及在现实生活中,找出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东西。”这句话也可以说是汉德森非洲之行的最好注脚,他要找寻的正是人生基本的、持久的、本质的意义。贝娄最认同自己创造的这个人物并非是故作姿态,而是其根深蒂固的犹太文化意识所致。他的绝大多数作品都可以看作是其驳斥西方文明注定要腐朽没落这一论调的努力,这与他否定虚无与绝望、坚信人类生存价值与意义的犹太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贝娄对汉德森非洲之行的设计表明了其严肃的道德立场。汉德森的非洲之旅是其内心矛盾与煎熬的戏剧化展示,是他饱尝磨难寻求真我和人生意义本质的探索历程,是贝娄展示人心之光明的一次大胆尝试。通过与两个非洲原始部落的接触与交往,汉德森的生存意识从混沌走向清明,他克服了原来对人对己、对整个世界的忿恨和对死亡的恐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要从孤寂的坟墓里站起来”。在阿内维部落那里,他学到了第一个最好的生活法则:人总是要活下去的,不但要使自己活下去,也要使每个人都活下去,生命总是神圣的;在那里,他还切身体会到了从前一直在口里叨念“对待罪孽要永远宽大为怀”那句话的真实含义。在瓦利利部落,他认识到了人对自己、对他人、对社会所担负的责任,坚定了他那灵魂不死的信念,深刻体会到了人的尊严、爱的意义和永生的本质。“我心中有个声音在说:我要!我要!我要?我?它应该对我说,她要,他要,他们要。再说,是爱才使现实成为现实的。”“不管我得到什么收获,总是由于爱,而不是由于其他任何原因。”正是由于这些“高尚品质”的真实存在,人才不是“一个乖戾、虚荣、鲁莽等等的皮囊……一个地道的地下廉价商品店出售的各种畸形商品”。贝娄用汉德森的精神净化过程告诫世人:视人为无物的虚无主义思想是现代人苦闷、彷徨、恐惧的根源,人类的苦难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地狱生自人心。
贝娄对现代派文学的不满是众所周知的,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无法接受现代派作家在他们作品中表现出的荒原意识。现代生活的诱惑是贝娄小说一个永恒的主题,芝加哥和纽约这两个现代工商业大都市代表了这种诱惑的方方面面,它们也蕴藏了对贝娄所说的“高尚事物”进行围攻的所有敌对势力。“如今,婚礼请柬往往叫人们想起离婚的统计数字,性关系的不稳定,以及对性革命和花柳病的思考,对疱疹和艾滋病在婚姻忠实方面所致结果的思考。在我们的思想里,孩子们也占有一席之地,关心他们的监护和养育,挂虑着他们受到成人的骚扰,以及日间托儿中心的问题。孩子们给丢在那里,这样,他们的父母就能腾出手来,从事自己的事业,或者欢庆两性之间充分的平等了。环绕着成长之中的孩子的,就不再是监狱的阴影,而是对于未来吸毒成瘾和犯罪的恐惧。”对伦理道德问题的质询、对虚无主义谬论的驳斥是贯穿贝娄全部作品的一个核心。《雨王汉德森》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贝娄对当时流行的现代虚无意识的一次宣战,他在这部小说里对现代人的身份进行了新的定义,对人类在荒原里生存的道德准则进行了新的阐释。汉德森这个人物向读者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道与仁爱是现代人摆脱焦虑和异化生存状态的一条途径,现代世界的疯狂与混乱并不能决定人类命运的走向,这正恰当地反映出了传统犹太文化对人道主义和道德行为的强调,如古犹太先哲所言:“爱邻居如爱你自己。”或许有人认为如此的老生常谈根本不值得一提,但整部《摩西五经》(TheTorah)向犹太民族传达的中心思想也就是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贝娄坚信经历了奥斯维辛和种族灭绝灾难的人类社会更需要重新认识人道主义和人性本质的重要意义,它们是人类社会健康成长的伦理基石,这是贝娄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主题。
虽然人们总是强调犹太文化的宗教色彩,其实犹太哲学是根植于现世和人生的哲学,它尊重生命的神圣、主张人道和善行,它强调社会、集体的价值,爱邻如爱己的理想也只有在人类集体背景下才有意义。贝娄全部作品实际也都在探索他在文学创作之初就提出来的问题:“好人应该怎样生活?”犹太文化强调历史的记忆,强调家庭与社会生活的伦理价值,整部《旧约》实际上也是一部家族的历史,回归社会生活是贝娄作品所要阐述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一主题在《雨王汉德森》这部小说里表现得更加直接与明确。经历了各种磨难后的汉德森迫切希望回归社会、回归家庭、回到妻子莉莉的身边,这与非洲之行前的汉德森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在二十天之内成熟了二十年。” 省级论文发表汉德森在回乡之前写给莉莉的一封长信实际上是对他一生经历的回顾和反思。在小说的前四章,莉莉的声音完全被汉德森的辱骂和叫嚣淹没了,从汉德森的话语里,读者认识到的莉莉形象是虚荣、邋遢、挥霍成性、谎话连篇,满口善恶、生死、真假、爱憎之类的说教却连自己的内衣都不及时换洗,整天摆出贵妇主人的架子,家里却脏乱不堪。汉德森总是对她的说教冷嘲热讽,甚至恶语相加,私下责骂她,当众喝斥她,但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在这部小说里,莉莉是爱赋予人生意义这一理论最主要的倡导者,汉德森讲的故事一直就在向这个方向发展。莉莉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正像汉德森最后认识到的那样,她的最大美德就是具有爱的能力。“她对贫民区居民很友好,尤其是老家伙和老娘们最要好。她说她理解他们为什么尽管靠救济金过活还买电视机。她让这些人把他们的牛奶和黄油放在她的冰箱里,还代他们填写社会福利登记表。依我看,她认为她是在为这些移民和意大利人做点好事,向他们表明一个美国人的心肠有多好。然而她确乎是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的,她热情洋溢地跑来跑去,说上许多不相干的话,同他们搭腔。”她父亲是个酒鬼,是家里的暴君,但“莉莉从不愿听人讲她父亲一句坏话,为他的事比为她自己的事还更容易动感情。她还把她老子的相片随身带在钱包里”。她不停地对汉德森说“我爱你”,但这种自然而然的情感表白却让汉德森心烦,这样的话语,他自己甚至在娶莉莉为妻的时候也没能说出口。但非洲之旅终于让他敞开了心扉,在给莉莉的信上写出了这样温情的表白:“莉莉,我也许最近有好些时候都没有这样讲了,可是我对你确实有着真诚的感情,宝贝啊,这种感情有时绞得我心痛。你可以称它为爱情,虽然我个人觉得这词儿全然是骗人的鬼话。”他在信中告诉莉莉把家里的猪全卖掉,代他给朋友送一件结婚礼品,替他在医学中心办理入学注册,还向莉莉保证“从今以后,一切都会不同了”。如果学医不成,他想申请干教会工作。总之,在小说结尾处,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充满爱心、急切要返回现实社会生活的汉德森,一个不再逃避责任、孤僻乖戾的汉德森,一个不停对他的非洲向导唠叨思乡之情的汉德森。“我一定要回到莉莉和孩子们的身边,在见到他们,特别是莉莉本人之前,我是不会安心的。我得了严重的思家病。因为我说:什么是宇宙啊?很大。那么我们又是什么呢?很小。因此我还不如呆在家里,我的妻子是爱我的。即使她仅仅是表面上爱我,那也比什么也没有强呀。不管怎么说,我对她是一片柔情。……不管她说什么都没关系,反正我不会因为她的说教而不爱她。” 省级论文发表
在回家的旅途中,汉德森还想起了他的父亲、他那溺水身亡的哥哥。他从前一直认为家里人把他视作另类,父亲根本对他没什么好感,父子俩从来没有办法沟通,只是因为哥哥死了,他才成为家产的继承人。现在他懂了,如果淹死的是他,不是哥哥,父亲也是会伤心落泪的,他此刻对家的回忆充满了温馨和柔情。贝娄在这里通过主人公对往事的回忆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幸福温暖的人生画卷,由于爱的存在,社会与人生才如此美好。尽管人性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完美,但人毕竟是按上帝的样子创造出来的,这正是犹太文化意识中最基本的一个理念。如DanielR.Schwarz所言:“文学文本的形式——其文体风格、结构、叙事技巧——无一不表现其价值体系。”贝娄在《雨王汉德森》这部小说里巧妙安排如同《旧约·出埃及记》一样的汉德森非洲之行这一故事情节,充分表达了他的社会伦理价值观念,非洲之行恰似一次对汉德森灵魂的洗礼,让他洗心革面,让他对生命的本质有了崭新的认识:人是社会的人,爱赋予人类社会生活以意义,天堂不在彼岸,不管人类本身还是人类社会存在着什么样的缺陷,天堂仍在我们身边,它只可能存在于有真有善、有美有爱的人间。
贝娄生长于一个正统的犹太家庭,意第绪语是他的第一语言,在犹太宗教学校学习过希伯来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我人生最易受影响的时候,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犹太人。那是一份礼物,一份无法争辩的好运气。”作为一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小说家,贝娄充分意识到了自己民族文化遗产的价值,热情讴歌人道主义和人的高贵品质,利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对20世纪上半叶盛行一时的物质主义、虚无主义、末世论等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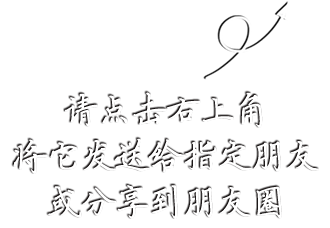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