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格利特对超现实主义艺术动机的证伪
2012年3月01日 13:44 作者:lunwwcom摘要: 马格利特持守着超现实主义艺术对经院派绘画的批判精神,却没有乞灵于超越现实存在的想象世界来获致自我本真;没有笃定于无意识梦境中的观看以捍卫绘画的独特性。他以平常心境在艺术与日常存在之间游走,醉心于“文本的愉悦”之中,反证了超现实主义艺术自律性诉求的虚妄性,从而开启了后现代艺术之门。
关键词:超现实主义;证伪;自律性;本真;他者引 言
弗•詹姆逊曾言:“作为超现实主义者中的独特一元,马格利特自现代到现代以后的巨变中浮现出来,成为后现代的一种象征:神奇的、拉康式的先机,却不露声色。”[1](p246)这个评价深谙比利时超现实主义画家雷尼•马格利特的艺术玄机:一方面,他持守着超现实主义艺术对经院派绘画的批判与重构精神,另一方面,他又没有像达利、恩斯特等超现实主义画家一样,借助无意识的自动创作营构一个与现实生活截然不同的诡异世界来表征自我的存在;没有笃定于无意识梦境中的观看以捍卫绘画的独特性。他以极其平常的心境在艺术与日常存在之间游走,醉心于“文本的愉悦”之中,他也因此探析到了超现实主义艺术对绘画本真的守护和对人本真存在诉求的虚妄性,从而打开了一道通往后现代艺术的大门。一、 以“被他者建构的画家之看”证伪
超现实主义的艺术造反动机
在现代派艺术家看来,西方自15世纪以来的经院绘画与当时的政治、宗教、道德等具有家族相似性,其在场性的“观看”是作为不在场的诸多社会叙事法则之隐喻而存在的,而秘密就在于它借助语言学原理预设了一条绘画材料(画面实在物)、图像(想象物)与事物(实际存在)之间的通约原则,成就“以画替物”的虚假同一性。因此,其本质就是一种经由言说(符号化传达)实现对差异性宰制的暴虐逻各斯,而这正是限制艺术真实和表达自由的纽结所在。超现实主义艺术即为打破这种虚假同一性的“话语型艺术”而诞生,它主要借助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将真实的观看笃定于无意识的自由梦境,以去除绘画身上的他律性重轭;用违逆日常事实而组合的突兀形象结构画面,以脱离古典绘画“言”与“像”的同一性法则,使绘画回到“纯视觉艺术”,从而呼应了 “艺术语言自身的独立价值”、 “绘画摆脱对文学、历史的依赖”等现代派艺术主张。马格利特最初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仰慕即源于这点艺术造反动机,吊诡的是,他却在一系列具有悖论性的绘画中将这种激进动机指认成了虚妄呓语。
在米歇尔•福柯看来,现代派绘画的突破路径几乎都集中在如何砸碎自文艺复兴以降沿用了五百年的“造型再现”和“语言指涉”的关系锁链上。在《这不是一只烟斗》中,玛格利特也展开了他的质疑。通常,观看绘画总是与概念化的语言活动同步展开——它是什么?它看起来像什么?它描述或说明了什么?换言之,观看视觉机能常常是认识行为的一个补充性过程。而在这幅画中,玛格利特通过“这不是一只烟斗”的置入却阻止了人们的观看习惯。这一中断既暗含着对绘画纯粹性的捍卫,绘画拒绝他者插手;同时强调了同为人类把握世界方式的语言与绘画具有不可化约性。“我们去说我们所看到的东西,这是徒劳的,我们所看到的并不寓于我们所说的。我们设法凭着使用形象的比喻、隐喻或直喻去表现我们所说的一切,也将是徒劳的”[2](p12) 。因此,词语与形象的关系成为一种根本不可能确定从属地位的相互比拟、同化或否定的无限过程。当我们习惯性地依循词语的指示去看绘画时,烟斗形象自然被抽象化的概念所同化,绘画与实物均被遮蔽起来,反之亦然。但当我们遭遇到这种矛盾关系时,烟斗、画像和语言的各自存在纷纷走上前来,谁都在力图挣脱另一个设定的阈限。毫无疑问,玛格利特已经触及到了西方文化的创伤性硬核——人到底能看到什么?看真的能脱离语言、文学等他者的牵绊而成为纯粹视觉性经验么?
康德指出,由于人的认知经验都来源并受制于现象,当然就不能够确证物自体是否和现象具有结构和秩序上的同一性,而人之所以能把捉到到对象都是由于先验范畴的作用。因此,事物的本真是无法接近的,无论是表象、词语、还是形象。《两个秘密》中马格利特给出了同样的担忧。大画框将小画框变成了一幅纯粹的绘画,而高悬的烟斗又促逼它作为一个能指陷入追索其所指的焦虑中——证明绘画形象与物体本真的同一性。然而,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物是“安于自身”、“守住自己”的自在、自持、致密或阴沉。我们感到石头的沉重,但我们无法穿透它;“要是我们砸碎石头而试图穿透它,石头的碎块也决不会显示出任何内在的和被开启的东西。石头很快就又隐回到……同样的阴沉中去了”[3](p33)。因此,该画中“烟斗的二重身”让我们看到,不但抽象的词语而且逼真的形象召唤也无法让真实的东西“苏醒”,实物的幽灵总会从词语和形象的结构或者驯化中逃逸出来,游弋在它们周遭,既挥掸不去,也无从触摸。在《阿尔贡之战》中,一团乌云旁边并置一块坚实的石块,证明了玛格利特不止一次地被“观看”的可靠性所困扰——反映在人视网膜上的图像事实是相当贫乏的,绝大部分的因素则需要人的想象加以填补。补充的过程就是表象的形成,“表象”即“透过现象看本质”,是对事物的一种“观念化”把握。而观念化“就是对最初已经丧失、被排除掉的(一开始就被压抑)的再现所做的符号性代指。[4](p48)”在《望远镜》中,画家让我们透过两扇透明的玻璃窗,看到了“蓝天与白云”;令人惶惑的是,从微微打开的窗户缝隙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漆黑一团。玻璃窗内外的情景出现如此大的反差显然是玻璃窗的狡计。“玻璃窗框架就像幻象-框架,正是幻象框架构成了现实”[4](p45),玻璃窗的出现让蓝天、白云在人的意识中呈现并得以固定,这说明人类的感知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性概念再现中才能形成对事物的表象,即人所意识的现实世界都只能存在于符号秩序(玻璃框就是人类的语言之隐喻)中。打开窗户一团漆黑,表征着离开了符号秩序我们什么都看不见。而问题的症结恰如在《这不是一只烟斗》中所证实的一样,就在于符号秩序与形象、事物的本真之间存在着恒久罅隙,它总是执著于当时当地单一的表达结构,既表达一定意义,又掩盖其他意义;只要符号秩序参与,观看就再也无法回复原初状态。而且,观看总是观者之看,而观者都是在一定知识、观念规训下成长的。故而,观看注定带上“偏见”。马格利特以《错误的镜子》诠释着:呈现在我们视觉中的映像与其说是自我感知结果,不如说是一定文化模式在其中的构作。所以,在通常情形中,我们“看到的”都是一些固定形式——蓝天白云,而真实的东西(眸子中的)却因为符号秩序的在场或压抑而被我们视而不见。《玻璃窗》中打开的窗子后出现的漆黑一团不是没有(空无),反而是绝对性的有。只不过这团真实的东西经过概念化的表象方式(玻璃框)过滤后被掩藏起来了,这就是拉康所说的符号化的剩余——实在界。因此,符号秩序不仅蒙蔽了事物的自在存在,而且制约了人的感知,先天命定了只能生活在由种种符号或形象所编织而成的秩序中的画家,他的“观看”总是被“他者”牵制着。
尽管经过了符号性秩序整流,真实的东西被压抑和割舍掉了,但正是这种缺失成了人类欲望的策源地。人总会不断通过想象和象征符号等虚构方式追寻。打开窗子,人就有可能去掉各种已经制度化的、二元对立的社会文化机构和规则系统的干预,进入感性直观层面中对对象进行把握。正如巴塔耶所说 “非知识就是暴露”, 胡塞尔所说“悬搁”“偏见”,就会“面向实事本身”。悖谬的是,实在界的本质就是被符号阉割后的剩余,无论那种靠近方式都是误把想象的所指当成真实的所指。只要是呈现就是对真实的误读或异化;一旦符号介入,实在界就会隐遁。超现实主义艺术执著于无意识的梦幻影像,就是深信这种观看的本真性。殊不知,这种所见也是被他者结构而出的。弗洛伊德的研究发现,梦有两个工匠:缩聚和位移。前者是把无意识中一些具有相似性和因果关系的因素聚合在一起,后者是对前者的整理。因而我们在梦中的所见就不是表面的图形,而是掩藏在图形变式中的符号:“字谜”。拉康因此认定,“梦具有某种文字形式的结构”[5](p106),是一种象征潜藏在人的无意识中的现实生活和欲望的图式。这样人在梦中所看到的依然是在一定符号秩序中呈现出来的“真实”。无论是达利画中被蜂蛰的女人体还是米罗画中的线条,我们都依稀看到被现实生活法则整流的痕迹。 在《人类的命运》中,玛格利特最终告诫我们,没有符号幻象的支撑,我们无从认识并进驻现实,只有把幻想的东西当成实有加以诠释,所以表征出的只是故事的一半,另一半则“处在没有说出,但被幻想,被暗含却不能被显示的东西中” [6](p266) 。这就说明,画家展示出来的观看也是在一定 “框架”中进行的,它是那不可靠观看的异化,是“实在之物”的二度变形。“一言以蔽之,他说出的东西总是不同于他想说或打算要说的事物。”[7]( P239)
因此,玛格利特意识到了绘画的持久悖论——在被语言、文化等社会性叙事方式所结构的现实中,只有打破这些认知框架,才可能达到看的真实;而一旦打破了它们,画家又无从呈现自己的所看。因此,超现实主义寻求的“除却他者的干扰,绘画就可以将真实的事物召唤在场”的艺术自律性是假命题。二、 以“在现实中被谋划的身体”证伪
超现实主义对人本真存在的假定
超现实主义的另一个艺术动机在于建构一个与受制于工具理性、形而上学、世俗欲望的现实世界判剖有别的超然境界,籍此来诉求人的本真存在。布勒东声称,超现实主义的价值就在于让人类重新发觉精神世界中一个被眼前物欲世界遮蔽,但又最为重要的部分。“超现实主义竭力想摆脱日常生活的单调和沮丧,声称梦是唯一的希望。他们转向自己无意识的非理性世界,抛弃了一切时间羁绊和道德判断,把来自过去、现在和错综纠结的心理状态的彼此无关的梦之体验组合在一起。”[8]( p222)达利为此作出了有力注脚。他不仅凭借艺术甚至生命的妄想狂方式执意要捅穿现实的虚伪性面纱,释放出真正属于本己的创生能量。可见,超现实主义乞灵于无意识转喻意欲获致一种改变生活、改造世界的意识形态颠覆力量。马格利特既坚定地秉承着这种革命精神,却又在艺术与日常存在游走之际证伪了作为个体本真存在诉求的超现实主义艺术诉求。
《强暴》一画就是超现实主义者玛格利特的阴毒“弑父”证据之一。在该画中,一个女人的躯体变成了她自己的面孔,乳房变成了眼睛,肚脐变成了鼻子,生殖器则变成了嘴巴。因为画家的确曾经看到了淹死的母亲裸体,很多艺术史家就将该画指认为自我惩戒的心理绘画。孤立地看此画,这种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角度作出的解释似乎不无道理,但将它与《向麦克•赛内特致敬》、《红模特》、《幕间休息》、《恋人》、《导游》、《女人酒瓶》等类似性作品比照在一起,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原来,玛格利特一直都在塑造一些无面孔的身体,像面孔被鲜花遮蔽的女人和被苹果替代的男人;背对观众的绅士;蒙着头巾接吻的恋人;被喷火的喇叭替代头部的导游甚至一些纯粹的肢体形态等。可见,玛格利特并非在挖掘身体的心理学资源,而是在考量一个有关身体的话语机制。身体一直是西方话语权的交锋和呈达之所,福柯发现,“文明社会”就是一个将人的身体划归于各种权力关系中进行规训的全面控制社会。权力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毛孔中,预设种种规范并慢慢侵入人的机体,促逼个体矫正身体中那些非规范性部分,形成社会化身体。这就是西方文化假以理性化之名而行扼杀以身体为核心的非理性之实,从而达到将非理性因素转化为理性权力之回声的集中体现。因此,社会对个体的掌控不是依托血腥压制而是借助经过理性文化造就的个体的自我监视和拘囚。玛格利特创作的这些没有面孔但行动自如的身体,看似突兀,实乃真切,这就是人在现实语境中的真实生存样态。四散的大地上,到处都是体面的人,可体面的人何曾有自由,有哪一个心灵上未曾戴上沉重的镣铐,有哪一个不是戴着坚实的“面具”。而正是这些失却了自我存在的机械化、无个性、木偶般的零散性身体构成了社会总体性生活图景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谁操控了“僵尸之舞”?玛格利特和拉康都将其认定为“他者”。
拉康认为,人的自我认同始终在“他者”的庇佑下,也因而落入“他者”的掌控中。最初,幼儿在镜子中发现了“自我”,便把这个虚构镜像认同成了“本真自我”。接着,幼儿将父母、小伙伴等他人对自己的纳受标准当成“人”的标尺,“人在看自己的时候也是在以他者的眼睛来看自己,因为如果没有作为他者的形象,他不能看到他自己。” [9](p220 )个体关于自我本真的描画又一次误入了他者彀中。最后,个体为了获得社会性认同,必然要依附于由语言、风俗、习惯、法规、宗教等构成的社会生活表征体系之网,个体对主体性的理解就是被其俘获的结果。而“表征体系”本质上都是些自相指称或自相参照的能指链,是它们结构着现实世界的意义。因此,这些先在的能指网络对个体具有一种存在论上的强暴关系。个体的一切言行与其说是自己决定的,不如说是被这个能指网络所控制而做出的应答。因此个体的心中总有另一个在能指网中被建构出的理想性我——“大写他者”存在,而这个他者常常占据了真我的位置。正是在这一文化层面上,《强暴》自曝了一个主题性悖谬:作为他者的强暴者,从未露脸,但其“凝视”依然在场;完全失却了标志之脸的被强暴者却通过身体的方式展示着“被看”的焦灼。这就反讽式地裸裎着一个社会性症候——任何个体要获致社会生活的话语权,就必须得到诸多“他者”的认同,主动接受其强暴。否则,就会被主流文化区隔在外,甚至被“认异”成不正常的人。因此,《强暴》中被强暴者不是女人的身体,而是个体的意识领域。就像女人不再是具体的个体,而是身体的表征一样,任何个体总是以“他者”期待的形式而在社会生活舞台上表演的。即个体关于自身的认同总是被他者虚构着。边沁的虚构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任何话语本质上都是一种虚构,符号性再现与原物之间具有不可通约性,但如果没有一种虚构性实体可以借助,就无法交流和思考。因此,对主体的符号性虚构既导致主体本真的永久遮蔽,又为他的社会性存在提供唯一可靠保障。玛格利特在女人与酒瓶的绘画中对此作出了策应。成熟 “女人”身体的诞生总是伴随着诸多印痕,女人总是在一定的网络和框架中被型构出来。在拉康看来,“女人”在西方父权制中心文化中是名实俱无的,如果说男人是符号界拥有阳具的主体的话,那么女人就转换成了阳具化的角色,女性被想象成一些具体的身体部位,是男人的幻想性客体,不是另一个与男人对等的完整的个人。因此,这些网络和框架本质上就是作为权利话语中心的男人之眼,是一些预先设定的社会性幻想结构,是它们为女人这个能指赋予了所指。可悲的是,任何女人都在倾其一生之力追逐着这个能指。因为角色就是被认同的能指,一旦偏离了它,人就可能被拒斥在现实文化之外。玛格利特的作品让我们知道,对于个体而言,他者如影随形却从不现形,从不言说却借助我的嘴巴唠叨,人的存在总在他处。故达利一生致力的反现实强暴努力其实是一种意淫。
最为恐怖的是,在《孤独行者的想象》、《恋人》等作品中,真正的“自我”早已经死去,替代我言说和行动的是一具永远看不到面庞的皮囊——空空如也就是现实生活中人的本真,超现实主义者标榜的绝对自由的无意识领域也被玛格利特彻底证伪。拉康发现,“无意识不是初始的,也不是本能的,它所知道的基本的东西只是能指的基本单位。”[9](p454)个体的主体意识是在言语活动中形成的,而言语意义生成在语言结构中。结构超越对话双方,对言说者的话语行为起着一种说话主体无意识的规范作用。即言说中我们意识到的东西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结构”形成的我们对语言的无意识应答,这个外在的“大他者”之潜在力量的构成了人的无意识。所以“无意识是大写的他者的话语”[9]( p417),不是生物性的,而是文化产物。因此,达利等超现实主义者对自我本真预想的悲剧性就在于,任何关于人的原初境遇的想象都不是前思维,前语言的,也是在语言中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妄想狂在幻想性认同中追逐的另一个对象性自己不是个体生理本能的转换,而是在一些个体之外的“社会张力”中形成的。所谓的无知无觉的疯癫状态和梦幻境态恰恰也是人在接受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更强大魔鬼“他者”规训的结果。玛格利特一些描述绘画创作的作品,画画者被画出来,画者眼中的蛋不自觉中成了画布上的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通常情况下,不是画家在画画,而是画在画画家。“不是个人的意识在说出语言,而是无意识语言在通过个人的意识而说话。”[10](p99)先在的绘画形式、语言、审美意识等构成了画家对绘画的无意识反映。
由此可见,玛格利特的艺术让人们惊悚地发现,超现实主义画家笔下对决现实世界,寻求本真自我的幻象世界本质上都是“他者”借用画家之笔戏说的本不存在的故事。海德格尔的“艺术是真理的自行置入”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假设。结 语
玛格利特对超现实主义艺术的证伪其实是在指责现代派艺术革命的不彻底性。因此,在他看来,绘画艺术只有从“一切都木已成舟”的观念中解脱出来, 即把它自我预设的艺术定义和语言结构消解,让不能解释任何东西的形式结构的不稳定性显现出来,才是自由的。艺术的本真即在通过不追求任何确定意义的自由创造活动,开启一个无边无际的、非同一性的模糊领域。作品既是形象,又是能指;既是言说,又是实在;既是有,又是无……是它们之间彼此对立、篡改、逆转、召唤和衍生的游戏,游到哪意义就生成在哪里,既不向谁服务,也不要谁臣服。绘画与装饰、艺术与日常生活、创作与意念、艺术家与非艺术家之间的差异也定然敉平。于此而言,玛格利特是一座从现代派通向后现代艺术的桥梁。参考文献:
[1]转引自耿幼壮.破碎的痕迹[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法]米歇尔•福科著.莫伟民译.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3][德]马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林中路[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4][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实在界的面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47.
[5]方汉文.后现代文化心理:拉康研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
[6][英]斯图尔特•霍尔著,徐亮,陆兴华译.表征[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266.
[7][斯洛文尼亚]斯拉沃热•齐泽克著,季广茂译.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147.
[8]凯瑟琳•库赫.分解:现代艺术的核心[A].激进的美学锋芒[C].周宪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法]雅克•拉康著,褚孝泉译.拉康选集[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94.
[10]夏光.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A].见:谢立中、阮新邦主编.现代性、后现代性社会理论:诠释与评论[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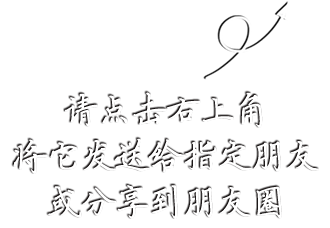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