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继伟
论文关键词:行政规范性文件 行为属性 行政行为
论文摘要: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在我国当前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由法院对各种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违法进行审查已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对行政机关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属性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其行政性、执行性的特征,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而非立法行为,这是我国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的理论前提。
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在我国当前是一个日益严重的现象,如何对行政规范性文件实施有效审查监管,减少和遏制行政规范性文件违法现象的发生,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由法院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违法进行审查,越来越受到学界的重视。司法审查①作为一种局外的、有严格程序保障的、最受社会各界和公民信赖的审查方式,应当担负起审查监管行政规范性文件的重要职责。由于我国实行人大至上,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这种政治架构决定法院不能对人大的立法行为进行审查,只能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所以,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首先要解决的理论前提是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在性质上究竟是立法行为,还是行政行为。
一、行政规范性文件之界定
党政行政论文发表 行政规范性文件是个理论上的概念,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界定。如“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执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对社会实施管理,依法定权限和法定程序发布的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行为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令。”[1](p177)“本书所说的规范性文件是指除法规、规章以外的由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2](p154)“规范性文件即行政规范性文件,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布行政法规和规章,请示和答复问题、指导、布置和商洽工作,报告情况和交流经验而作的具有法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除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外的抽象行政行为”[3](p168)虽然学界对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定义没有达成一致,但大多学者倾向于把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排除在行政规范性文件之外另行讨论。②本人认为,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规章以下的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都是由行政机关而非立法机关制定的,属性上应当是相同的,都属于行政规范性文件的下位概念,只是位阶不同,一个有名,一个无名而已。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就‘行政规范性文件’这一概念而言,虽然限定于行政法领域之内的规范性文件,但广义的解释是指所有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和行政规章在内。”“‘行政规范’是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相并列的、模式化的概念,一并位于其上位概念——‘行政规范性文件’之下。”③另外,从我国的立法实践来看,行政诉讼法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标的只能是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而在学理上与具体行政行为相对应的,被排除在受案范围之外的行政行为,即《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项所列的“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等”,则被称为抽象行政行为。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条则进一步明确规定:“《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项所规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是指行政机关针对不特定对象发布的能反复适用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可见,我国行政诉讼法也是把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行政规范性文件归为一类的。
所以本文把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置于行政规范性文件概念之下,将行政规范性文件概念界定为各级各类国家行政机关为贯彻执行法律,实施社会管理,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行为,依法制定、颁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各种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公告、命令、通知、批复、指示、决定等等在内。
二、行政规范性文件制定行为之属性分析
当前我国不少学者之所以反对对行政规范性文件进行司法审查,一个重要理由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特别是国务院行政法规的制定在本质上属于立法行为。根据我国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立法机关之下,共同对立法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司法机关对立法行为只能执行,而不能质疑,所以对行政规范性文件不能进行司法审查。那么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究竟是不是立法行为呢?
目前我国学术界对“立法”这一概念有各种各样的定义,概括起来可分为三种:一种是泛立法主义,认为凡制定抽象的规范性文件的行为都是立法,不仅制定规章的行为是立法,而且各级政府包括乡政府发布文件的行为也是立法;另一种是广义立法主义,认为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的行为都是立法,制定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不是立法;再一种是狭义立法主义或称为宪政主义,认为只有权力机关制定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的行为才是立法,其他都不是立法。[4](p160)笔者赞同狭义立法主义的观点,只有民选的代表民意的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才是立法。立法最本质的东西是创设新的权利义务,通过对公民权利义务的影响达到对社会的调控。而按照人民民主和社会契约的政治理论,人民是国家主权的享有者,对人民的权利义务施加任何影响就必须经过人民的同意,所以,在代议制之下,立法权应由民选的立法机关来行使,而不能由行政机关来行使,这是民主、法治的根本要求。“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每个人都被认为具有自由的精神,都应该由自己来统治自己,所以立法权应该由人民集体享有。”“如果立法权和行政权集合在同一个人或同一官吏团体的时候,自由不能存在。因为人们担心同一君主或立法机关制定专制法律,而以暴虐的方式执行。”[5](p158)“立法权,从它的理性原则来看,只能属于人民的意志,因为一切权利都应该从这个权力中产生,它的法律必须对任何人不能有不公正的做法。”[6](p140)我国宪法第58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也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而行政规范性文件也是权利义务规范,也能对人民的权利义务产生影响,为什么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行为又不是立法行为。原因在于行政规范性文件只是对法律的细化和贯彻落实,是执行性的,它不能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关系,在性质上应当是行政行为而非立法行为。
法学论文发表 第一,国家行政机关的执行性质在我国《宪法》中已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正因为行政机关并非权力机关,所以行政机关颁制的规范性文件,即抽象行政行为的产物并不能创设新的权利义务,否则,将偏离执行性的行政本义。另一方面,抽象行政行为作为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表现形式,其“抽象”性质实质上同样是具体而个别的,只是在行政行为这个范围内的,是相对于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的。相对于宪法意义上的制定法律的行为来讲,它是具体的。换言之,抽象行政行为这种基于法律之实施而制定规范性文件的行为,依然体现着行政权的执行性、具体性。因此,行政机关的抽象行政行为不能与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相提并论。
第二,在我国,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是以“根据”为原则的。宪法第89条第一项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宪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各部、各委员会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内,发布命令、指示和制定规章;地方组织法第60条第1款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制定规章,报国务院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以及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可以说,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追根溯源,最终都必须以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为根据。所谓“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把某种事物作为结论的前提或语言行动的基础。”既然是前提和基础,我们可以推断,在没有法律这个前提和基础的情况下,是不能先行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在有法律这个前提和基础的情况下,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也必须忠实于法律,不得随意篡改和变更,特别是对相对人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规定,更是不能随意增加、改变或取消,否则就违背了“根据”原则。而对于另外一种情形,授权立法,行政机关根据授权虽然可以创设新的权利义务,但这并不是没有限制的,它必须根据授权机关的授权,不得违背授权的范围和授权目的,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根据授权立法所制定的行政规范性文件仍是执行性的,只是它所执行的不是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而是权力机关的授权罢了。
第三,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虽然在形式上具有立法行为的特征和规律,但与权力机关的立法还是有本质差别的。行政机关实行首长负责制,其规范性文件的颁行遵循的是效率优先的行政程序,而不是“合议”的立法程序,故而抽象行政行为先天地缺乏充分反映民意的制度基础,使得其法律效力处于有争议的待定状态。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法律之成为法律,其“所绝对必需的条件,即社会的同意”(洛克语)。故而行政规范性文件的制定行为先天地缺乏充分反映民意的制度基础,它只是套用了“立法”的名称,使不少人把它与议会的立法行为混同起来。实际上,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机关可以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只是一种规范制定权,是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实现从个别管理到批量管理的转换,是管理数量上的变化,性质上并没有改变,仍是对法律的执行,属于行政权,是行政权的下位范畴。正如行政法学者孙笑侠所言,“行政权又可分为规范制定权、命令权、组织权、证明权、审批权、检查权、处罚权、强制权、调处权、裁决权、监督权、许可权等等,从而构成行政权力体系。”[7](p198)另一位学者姜明安也认为,“广义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规章和其他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其形式有决议、决定、规定、规程、公告、通告、布告、命令、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相对于法律来说是执行性的,是为执行法律而将法律的原则性条款具体化。因此,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属于广义执法的范畴。”[8](p148)“行政立法的性质:行政立法属于行政行为。”[9](p143)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551节第13款规定:行政行为包括行政机关的法规、裁定、许可证、制裁、救济的全部或一部分,或者和上述各项相当或否定的行为或不作为。这也说明了行政机关制定行政规范性文件属于行政行为,而非立法行为。
另外,虽然立法法对我国行政机关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行为作出了规定,但这一规定是基于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制定具有一定的立法特征和规律而作出的,而并不意味着它们在行使着国家立法权,也不意味着它们和立法权有相同的性质和地位。特别是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应否纳入立法法的调整范围,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将它们在立法法中作出统一规定,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对这一行为进行严格规范,而不是说制定规章的活动本身就是立法。
建筑类论文发表 还要说明的一点是关于国务院自主行政立法权的问题。宪法第89条第一项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行政措施,制定行政法规,发布决定和命令。目前国内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根据该项规定,国务院可以在没有上位法,没有授权的情况下直接依据宪法自主立法,确立新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而使国务院分享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对此观点本人不敢苟同,照这个说法,“根据宪法和法律”的“和”字就等于“或者”了,当法律空缺时,就变成了“根据宪法,在与法律不抵触的前提下”。这样理解并非宪法的本意,毕竟“和”与“或者”是有很大差别的。更何况让国务院分享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权与法律必须征得社会同意理论相违背。虽然在我国实践中的确存在国务院在没有上位法,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自主立法的事实,如国务院关于新闻出版、宗教自由、社团管理等方面的行政法规就是如此。但现存的不一定就是合理正确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立法任务又繁重,而立法机关又较弱,行政权力相对较强,为满足现实行政管理的法律需要而顺势分享了立法机关的立法权,这只能是权宜之计。如今条件成熟了,必须把它纠正和理顺过来,由立法机关把这些行政法规上升为法律,填补法律空白。如这两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就把国务院颁布的《公务员管理暂行条例》和《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上升为《公务员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
国务院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必须严格根据法律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对没有相应的上位法律,立法机关没有相应技术力量,现实又需要制定的行政法规,必须由权力机关授权国务院制定,国务院不应享有自主行政立法权。这样,在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上,既坚持了“人大”(国会)至上制度,保证立法权始终掌握在由人民选举产生的、能直接反映公共意志和要求的国家权力机关手中,以保证立法的民主性;又能提高国家的管理效率,保证国家行政机关有足够的权力对社会进行有效管理,以实现立法的灵活性、能动性。正如学者所言:议会立法至上,无法律即无行政,行政之准据唯制定法是也,立法务求细密,避免概括条款,习惯法、法理及司法判例、行政解释均不得为行政法之法渊源,行政规章命令不得为拘束人民之规范成为近代立法国之基本信条。[10](p67)
从以上分析得知,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行政法规的制定行为在本质上属于行政行为,而非立法行为。那么,司法机关作为与行政机关并列平行的机关,作为专司判断的司法机关,肩负监督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贯彻落实的重大职责,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对行政规范性文件是否违反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这是权力分工制约的体现,也是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促使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现实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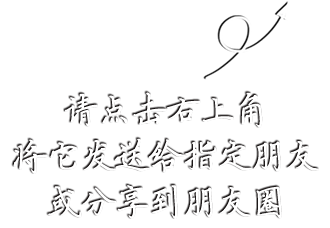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