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寻求自我历史限度的文化批判——从《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到《死火重温》
2010年12月06日 15:47 作者:职称论文论文网(www.lunww.com )是期刊推广、论文发表、论文写作指导的正规代理机构,我们与4、5百家省级、国家级、核心期刊有合作,我们合作的期刊都是万方、维普、中国知网、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收录的正规期刊。合作的期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可查,详情可来电0519-83865052,或者QQ:85782530咨询。
在激情澎湃的80年代末期,年仅28岁的汪晖在完成了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后,写下他在鲁迅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时隔七年之后,《死火重温—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一文是他面对80年代以来鲁迅研究成果的一次批判性反思和开拓。在从“此”到“彼”的道路中,汪晖在鲁迅研究中的思想探索轨迹并不是我的学识所能够把握的,也不是一篇小小的文章可以回答的。我所思索的是,能否在这个过程中就我关注的问题给出自己的回答。我的问题是:构成这一转变的路径的关节点在什么地方?这种转变又给今后鲁迅研究带来哪些可供开拓的思维空间?本文试图探寻在这七年间,汪晖从“目的”与“方式”间困境的自我反思开始,从对现代中国思想中心概念隐含的历史限度的分析到对鲁迅自我认同以至文化批判的侧重,其鲁迅研究意向的变化伴随着他对中国现代性问题及现代中国认同的思索,所有这些努力都为开拓鲁迅研究以至现代文化批判提供了历史可能性。
一、从“方式”到历史限度
或许有人无法完全认同其中的观点,但却无法回避《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一文中汪晖对在他之前中国鲁迅研究做出的反思时所提出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批判者与批判对象之间在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同一性,使丸山升先生看出此论文在反思过程中凸现出的“目的”与“方式”之间的矛盾性。那种斩钉截铁式的与旧的研究方式告别的姿态本身以及创造崭新的研究方式的希望存在着深刻的矛盾。正如加达默尔所说:“精神科学的研究不能认为自己是处于一种与我们作为历史存在对过去所采取的态度的绝对对立之中。在我们经常采取的对过去的态度中,真正的要求无论如何不是使我们远离和摆脱传统。我们其实是经常地处于传统之中,而且这种处于决不是什么对象化的行为,以致传统所告诉的东西被认为是某种另外的异己的东西—它一直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一种范例和借鉴,一种对自身的重新认识,在这种自我认识里,我们以后的历史判断几乎不被看作为认识,而被认为是对传统的最单纯的吸收或融化。”虽然汪晖在这篇文章中有对传统复杂性的分析和尊重,但告别过去、“回到五四”的激情同样使我们无法回避作为五四思想启蒙的重镇之一的鲁迅研究中所形成的思维方式(传统与现代、野蛮与文明等一系列的二元对立),这种方式为我们开拓了思维空间的同时,也建构了这个时代陈述的历史限度。
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明确自省,写于1992年的《绝望之后—(无地仿徨>自序》一文中,他对自己在写完《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之后思想的变化进行了反思:“对过往的一切所作的意识形态批判并没有逻辑的导向一种崭新的形态出现”。在所要达到的目的和方式之间的内在矛盾的困境处,他找到这种“方式”与近代中国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的渊源的密切联系。而这种主义“表达了一种对于否定性的理性批判的无条件信任。”试图突破这种困境进行自我质疑的第一次尝试是1989年写下的《预言与危机—中国现代历史中的“五四”启蒙运动》。文章侧重于五四启蒙运动的“目的”与它的“方式”之间蕴涵的五四启蒙思想的内在困境和危机。如何解决此困境的探索开始于这年下半年写作的((中国的“五四观”》。这是一篇探索历史事实、对历史事实的建构以及建构者本身在建构中所表达的观念体系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文章,在什么是“真实”、“真实”的历史前提是什么以及这一前提与某一集团的利益或生存方式的关系怎样等研究方面,每一种观念对五四的建构的合理性以及偏见和限度,成为汪晖此文反思“五四”的路径所在。如他自己所说,这是一个从“寻求真实”到对“真实”这一概念的自我质疑,再到对用以构造“真实”的那些前提的反省的过程。这种对研究对象历史限度的观察和思考开启了他关于鲁迅研究甚至是学术研究的新的意向。
当探索构成人们理解现代历史的重要概念的行为成为一种选择时,“先清理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的一些基本概念或话语及其在运用中的变异”,“通过分析某一概念及其与相关话语的关系,或许可以复现一个时代的各中心概念的关系网络及其演变,可以观察‘中国思想在现代延续’的内在过程。追寻这个思路,我们不难看出汪晖在从“方式”到对历史限度的探索中,不断展现出一条艰辛而又充满挑战的路途。
二、从“概念”到自我认同
从“中国思想在现代的延续”视角观察核心概念及其在中国的运用方式,通过对内嵌于中国传统中的概念的运用又实在不能等同于西方语境中此概念所代表的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常识的考察,发现并分析由于对“否定性的理性批判的无条件信任”而形成的晚清以降中国现代思想中所谓的思想路向,指出现代中国走向现代过程中对西方思想文化概念翻译中的“中国化”问题,这对谁来说都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刘禾认为:“知识从本源语言进人译体语言时,不可避免地要在译体语言的历史环境中发生新的意义。译文与原文之间的关系往往只剩下隐喻层面的对应,其余的意义则服从于译体语言使用者的实践需要”这个复杂的问题又是如何被向前推动的?正如“所有作为问题追问的问题作为对当时被追问的东西的回忆乃是现在被追问的问题;一样,1992一1993年在美国中国研究中心的学习和研究,让汪晖调整了自己已经开始的在“概念”运用方式上的探索,转向中国现代性问题的思考,而这些也直接导源于他在鲁迅研究方面所拥有的基础研究。我们知道,汪晖是从1907一1908年间鲁迅早期思想研究开始学术生涯的。延续他以前的研究成果,汪晖在鲁迅研究以下论点上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反思相遇。他认为,深受老师章太炎先生思想的影响,在《文化偏至伦》和《破恶声论》等文章中,鲁迅对以下现代文化的偏至的批判和悖论性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从不同方向观察现代问题的线索。这种“偏至”表现在从鸦片战争以来一些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救亡”意识下对西方文化尤其是对以此文化为中心形成的似乎具有普适性的目的进化论所表现出的无条件祟拜。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中,民族主义的主题显示了其不言而喻的优先性。鲁迅在思考中国民族出路时提出“搐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沙聚之邦”可成“人国”以及“别立新宗”等,所有这些主张都是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上强调“自性”的重要。而“自性”的确立又和人们的自我认同紧密相关,但由于人们自己认识自己实际上不可能,所以必须在与他者的关系中来确定自我本身,而这种在自我认同中表现出的对现代文化的批判性反思又是晚清以降中国思想界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现代中国思想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其博士论文中对鲁迅精神结构的悖论分析一致,在1994年发表的((个人观念的起源与中国的现代认同》中,汪晖提出了鲁迅精神世界中两大悖论式的主题是批判主题与自知主题。正是由于二者存在才形成了把自我纳人到批判对象之中而加以批判的以“反抗”为核心、以“绝望”为出发点的鲁迅思想体系的框架。对这两个主题的分析导向中国现代性问题反思的是19%年发表的他翻译的福柯的((什么是启蒙》一文。“可以连接我们与启蒙的绳索不是忠实于某些教条,而是一种态度的永恒的复活—这种态度是一种哲学的气质,它可以被描述为对我们的历史时代的永恒的批判。;[6]这种批判实践寻求把我们所思所想、所作与许多历史事件连接起来的话语的具体实例,寻求我们是什么的批判(即对我们背负的限度的历史分析)将伴随着超越这些话语的可能性。批判的任务需要研究我们的限度,它是赋予我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形式的所在。这个批判任务如何可能完成?
面对西方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思考卷人追求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的中国现代性问题实际上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问题。写于1993年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一文中,汪晖首次提出中国现代思想具有一种“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特质的著名观点。1994年发表的《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一文通过对韦伯关于现代性的论述,揭示出韦伯有关现代性概念背后对其历史性的遮蔽及其对中国现代性问题进行分析和诊断的能力的限制。他认为,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首先必须对现代性的知识体系本身进行反思。这种反思应该从把中国现代性置于文化研究和历史研究的视野之中开始,并寻找相应的历史范畴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从而把中国的问题作为中国的问题来研究。
作为在中国现代性的知识体系中成长起来的学者,汪晖拒绝不加分析地把西方中心主义下形成的知识体 系作为唯一真理的做法,在自我认同中寻求文化交流中由文化主体间性所产生的成果,是他从鲁迅研究中得出的结论,也可能正是批判性知识分子群体应有的选择。1995年10月在《汪晖自选集》自序中,他指出:“中国的现代历史是被现代性的历史笼罩的历史,是以现代性的历史叙事为前提的,因此,在讨论中国的现代问题时,需要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现代中国思想的内在复杂性和矛盾性正是中国思想对现代性的悖论态度,在悖论中显现了现代性的内在紧张,中国现代思想本身,仍然应该作为我们反思现代性的主要源泉之一。”如何重建更为复杂的历史叙事?中国现代思想比如鲁迅的思想如何可以作为我们反思现代性的主要资源?
三、死火重温与文化批判
1996年在为《恩怨录—鲁迅和他的论敌文选》一书作序时,汪晖写下了《死火重温》。这是一篇从鲁迅杂文创作出发对鲁迅研究以至现代中国思想研究思路进行了极大拓展的文章,也是对以上问题从一个侧面进行的答复。汪晖抓住了鲁迅之所以与其论敌进行斗争的关键所在,把鲁迅文化实践的侧重点放在了鲁迅终生从事的文化批判方面,而正是在这些方面表现了鲁迅对现代中国思想的悖论态度和“永远革命”的文化批判姿态,这也正是《野草》中的死火的战士想象的表征。重温死火,汪晖认为,鲁迅文化批评的核心是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是从未同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模式相脱离的。而在统治方式形成和再生过程中,文化和传统为它们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鲁迅的文化态度使他从来没有把历史中的人物、思想、学派(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外来的)与权势的关系的考察分开过。因此,通过与论敌的思想斗争,寻求由传统和文化建构起来的历史图景遮盖着什么?不断创造出遮盖这种历史关系的“文化图景”或知识体系又是什么?这些在“自然秩序”中把各种形式的不平等合法化的知识体系产生的社会条件又是什么?鲁迅的文化批判实践就是对这些问题的回答。
正像加达默尔所说,“思想文化是对现实问题的回答。揭示这些思想文化的产生历史可以使这些问题具有某些不可避免的因素。被理解的问题不可能简单地视为我们的知识。它们变成了我们自身的问题。”也许,恰当的做法应该是对日益增长的对知识体系形成过程中社会条件和我们的历史限度的遗忘的批判性反思。鲁迅正是在这一点上恰恰以其文化实践为我们指出当代思想开拓的空间所在,促使我们思考各种知识生产方式的限度及其社会含义,反思我们身处其间的知识活动、我们的知识前提以及知识活动与当代社会进程的复杂关系,或许这会为我们揭示有关唯一性、永恒性和无可争议性的叙述只不过是虚假的幻象,从而为我们探索现代世界提供各种可能性。
如果说“一件本文在我们作解释时向我们提出的间题,只有当本文被当作对某个问题的回答时才能被人理解。那么,不同的解读者会因他们向汪晖文本提出的问题的不同而有不同角度的回答,也会被人们从不同的侧面进行理解,在这一点上,“谁理解,谁就在理解自身”这句话也许是永远正确的。但我们也应深知,我们“自身”却是深深扎根于我们所处的现代社会文化之中的,批判自我历史限度本身就是对知识分子使命感的一种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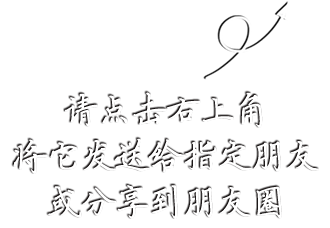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