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好像并不复杂,但一审、二审迥然相异的判决却至少可以透露出这样的信息: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原告以被告侵犯了自己对浩达商厦一层西侧大厅建筑面积380平方米房屋的优先购买权为由要求确认被告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无效的起诉,颇有“以一隅抗全国”的意味,其影响交易之便捷与效率显而易见,一审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也因此确有道理。可问题在于,原告对自己承租房屋的优先购买权是法律明确赋予的。进一步来想,在本案的背景下,若照一审那么判,法律赋予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合理性是否丧失殆尽?由此,要解决本案,首先要明确的是法律赋予房屋承租人以优先购买权的理由或说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存在价值。二审法院的判决其实变更了原告的诉讼请求——不是宣告被告间的买卖合同全部无效,而只是宣告买卖合同中转让原告承租的380平方米房屋的内容无效。乍看起来,二审法院的判决更加合理:既维护了原告的法定权利,也保护了被告间的楼宇交易。但这却掩饰不了对第三人保护的苍白——如果合同部分内容的无效将会给一方当事人带来巨大损害,那么执意维护合同的效力还有多大的意义?也许人家南洋新世纪公司早知不能完整地获得楼房的所有权就根本不会动意购买浩达商厦。于是,有关优先购买权制度的“陈年旧账”便被重新翻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和性质如何?租赁合同关系下的房屋承租人凭什么可以要求宣告别人买卖合同的无效?优先购买权行使的“同等条件”的内涵究竟包括什么?所谓“同等”,是绝对相同,还是相对相同?所谓“条件”是仅指价格条件还是兼包其他条件?是否必须要求房屋承租人所承租的房屋与出租人卖与第三人的房屋完全同一?本文力图在清楚回答上述问题的基础上,给出笔者对本案的看法。
一、优先购买权制度之检讨
(一)优先购买权的定义、历史及现状
中外学者及法条对优先购买权所下定义大同小异。[1]王泽鉴先生认为:“优先购买权云者,谓特定人依约或法律规定,于所有人(义务人)出卖动产或不动产时,有依同样条件优先购买之权利。”[2]王利明先生认为:“优先购买权,又称为‘先买权’,是特定的民事主体依照法律的规定享有的先于他人购买某项特定财产的权利。”[3] 《德国民法典》在“债权编”和“物权编”分别对优先购买权进行了规定。位于其“债权编”中的504条规定:“对标的物有优先买受权的人,在先卖义务人与第三人对标的物订立买卖合同时,可以行使先买权”。位于其“物权编”中的第1094条规定:“(1)土地可以此种方式设定负担,使因设定负担而受利益的人对所有权人享有先买权。(2)先买权也可以为另一土地的现时所有权人的利益而设定。”[4]我国《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郑玉波先生指出,优先购买权属于一种优先权,“为自由平等原则(如契约自由原则,债权人平等原则)之例外,有碍交易之敏活及交易之安全,因而于解释上及适用上均应从严,而不应从宽。”[5]
据学者考证,无论中西,优先购买权制度皆有绵长之历史。在中国,优先购买权制度最早可溯及北魏均田令。[6]唐律中有房地产买卖必须先问近亲,次问四邻,近亲四邻不要,才得卖于别人。[7]后经宋、元、明、清,优先购买权虽明见于律令者较少、以民间习惯存在者居多,但却一直得到官府的支持。[8]到民国初期,大理院判决再次予以明确肯定:“佃租他人之土地者,就其土地有利害关系,苟依该地方之习惯法则,租户有先买权利,番制衙门自应授为判断之准据,惟租户得以先买,则所有权人应当通知租户尽其先买之义务,不独限制所有权人之自由处分,且于地方之发达,与经济之流通,亦不无影响,故认许此种先买权,应以期间较长或无期之租户为限,使为短期佃租,或租约中订明随时可以解约者,则就其他利害关系尚浅,纵有习惯,亦不应有法之效力。”[9]新中国对优先购买权进行确认的法条较早见于1950年3月28日东北人民政府发布的《东北城市房产管理暂行条例》。[10]在外国,优先购买权制度则可寻根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先买权制度,在拜占庭时期至罗马法,即已有之,所谓Jus retractus者亦属一种先买权,德国普通法上之Retraktrecht一语,即由此而来。”[11]大陆法系诸国都以不同的形式规定了在特定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对继承中遗产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作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该法第815—14条规定:“任何共有人,均可在此项通知之日起一个月期限内,以司法外文书告知让与人,其将按照通知的价格与条件行使先取权。在共有人行使先取权的情况下,行使先取权的人,自向财产出卖人作出答复之日起,可以有两个月期限实现对该财产的变卖;过此期限,经向其发出催告后15天如无效果,宣告先取财产的权利无效,并且不防碍出卖人可能对其提出损害赔偿请求。”而《德国民法典》对优先购买权规定得更为详密,该法在债编和物权编各以11个条文规定了优先购买权,在债编以特种买卖形式予以规范,在物权编以物权形式确优先购买权。现代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大都规定了先买权。[12]
中国很多现行法规、司法解释对优先购买权作了规定,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8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230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35条第3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22条、《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10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等等。
上述法规、司法解释涉及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合伙人优先购买权、公司股东优先购买权等多种类型。鉴于本文所讨论的是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问题,本文只详细列出与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相关的法规及司法解释。
《合同法》第230条的规定前已述及,此处不赘。
《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须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
对上面三项规定,学者主要诟病在:(1)“提前三个月”的时间起点不明确。所谓“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是指出租人有出卖意向还是与第三人已进行磋商,抑或是已与第三人成立买卖合同?(2)宣告买卖合同无效是否合适?是否会损害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合同被宣告无效后,房屋所有权的归属不明,是回归出租人还是直接归属承租人?(3)同等条件的内涵不明。
这些问题也是本文后面所要着力探讨的。
(二)存耶?废耶?——优先购买权制度的价值
同很多其他悠久制度一样,走过漫漫风雨历程的优先购买权制度也在现今社会面临存废之争。这个问题其实在本文前面详细引述的那份民国初年大理院判决中已显露端倪——优先购买权“不独限制所有权人之自由处分,且于地方之发达,与经济之流通,亦不无影响”——只不过大理院的法官采用的是附上“期间较长或无期之租户”作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来进一步限制其行使,而现今有些学者则主张要彻底取消优先购买权制度。
这些学者所持的废止理由主要有:
(1)所有权一直是一切财产权的基础,是人对财产最充分、完全、强大的一种支配权。其权利的行使应当是自由的,原则上应不受干涉,这是私法意思自治的要求。因此出卖者在选择出卖对象、内容、价款、方式、时间和地点等的时候,应不受外界的任何影响才对。但是,优先购买权制度,却限制了出卖人在出卖财产时对买受人的选择权。
(2)所有者出卖自己的房屋,一般居于多种原因。比如急于脱手,使自己陷于困境的财政状况得以缓解。因此出卖的时机以及时间的要求对房屋所产生的价值是极其重要的。而优先购买权制度往往使出卖人在等待承租人答复的过程中错失良机,最终导致出卖人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得以实现,甚至于因时间的延误使得本可以成交的交易根本得不到实现。承典人的优先购买权,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亦是如此。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优先购买权制度妨碍了交易的速度,甚至于损害了出卖人的利益。
(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意见》(试行)第118条的规定来看,出租人出售出租房屋未尽通知义务致使承租人丧失行使优先权的机会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此规定仅考虑了出租人和承租人之间的关系,并未考虑到第三人即购买出租人房屋的其他人的利益,如果第三人有偿的、和平的、善意地取得了出租人所出卖房屋的所有权,但仍然会因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强大效力而最终落空。委实不利于交易安全的维护。
(4)不动产优先购买权实际上也妨害了社会的公平。购买机会本来就不应该先后有别,并且,不同类型的优先购买权发生竞合时,也会带来新的不公平。
(5)诱发道德风险。所有权人为避免自己利益受损,会积极采取“一房二价”等规避措施,防碍优先购买权的实现,并因此引起大量纠纷。
(6)同等条件的判断既让法官费劲为难,也会造成执法上的模糊与不确定,有碍法制统一。因此废除优先购买权制度,“岂不是皆大欢喜!”[13]
与此相对的,是捍卫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学者所列举的该制度应当继续存在的理由:
(1)贯彻某项社会政策,实现实质正义。优先购买权可以分为约定和法定两大类。[14]由当事人通过合同来设立的约定优先购买权,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法律及旁人自无法加以置喙。而法定的优先购买权多基于某种政策,如为社会政策而设。我国台湾地区《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第15条第1项规定,承租人于耕地出卖或出典时,有优先承受之权。这种耕地承租人优先承受之权即是一项基于“扶植自耕农”的基本社会政策而产生的重要制度。[15]而我国大陆民法规定的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也是为了照顾被推定为“弱者”的承租人利益,避免其依附于租赁房屋而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被骤然推翻,并有可能因之流离失所的危险。购买机会均等的形式正义有时有害于实质正义的实现,所以“国家通过法律允许承租人、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反映了在经济公平基础上国家对平等权所进行的修正,这是法律公平实现的更高层次。”[16]
(2)提高物之利用效率、促进物尽其用。首先,在共有关系中,因在同一物之上同时存在数个共同所有人,故就共有物的管理、使用及处分等事项,莫不需要个共有人的彼此容忍和通力协作才能达成一致意见。然而各共有人未必能够完全齐心协力,所以各国法律对此往往规定有详细的决策程序和决策方法,非依次达成的处理意见不生效力。而共有人除须一致对外,尚须就其内部的权利义务关系进行分配,这不免使共有关系更加复杂。由此导致在共有人较多的情形对物的利用效率必然低于在共有人较少或单独所有情形对物的利用效率。因此就某一特定物而言,共有不能不说是一种低效率的产权安排方式。或许正由于共有关系的复杂性,拿破仑法典的编纂者才奉行了这样一种颇具特色的法律思想:“既不承认共有,也不承认共有财产的状态,而仅仅考虑各个共有人的个人权利。”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共有关系在社会中的大量存在确有合理且必要之处,法律不能视而不见,否则不免贻人掩耳盗铃之讥。固为解决此一矛盾,法律乃有共有人先买权制度之设,即于一共有人欲出售其份额于第三人时,法律赋予其他共有人以在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的权利。如此既不损害出卖人的利益,又能通过先买权的行使来减少共有人的数量,从而简化甚至消除共有关系,以更好的发挥物的效用;其次,在不动产用益关系中,由于有益关系多时因用益人的生活或生产需要而不得已在他人的不动产上设立的,就不动产所有人而言,虽利于其发挥物的效益,但从有益权人的角度考虑,一方面,使用他人之物终究不如使用自己之物便宜、尽心,另一方面长期使用他人之物也不免使用益物权人产生寄人篱下、仰仗他人鼻息之感,因为毕竟“求人不如求己”。故法律赋予用益权人以先买权,意在于不动产所有人出卖标的物时,使其得以同等条件优先于他人而购买,一则可维护和稳定既有的物的利用关系,避免因利用关系被全部推翻重来而导致的成本浪费,使物的所有和物的利用合而为一,降低交易成本;二则可消除用益权人的心理负担,鼓励其更谨慎、合理的利用该不动产。并且法律在决定是否赋予用益权人以优先购买权时也相当谨慎——对于一些无偿的或在动产之上形成的物的用益关系,或因其为无偿利用,或因其标的为动产,价值较低,市场上容易获得,而没有赋予其使用人以优先购买权。[17]
比较上述反对和赞成两派声音,笔者更加倾向于后者。上述反对声音,固然有合理成分,但也都有可商榷之处。不论其他,单说优先购买权制度下尚有多项分类,不分皂白,一棍子打死优先购买权制度肯定有失鲁莽。细察各具体反对理由,亦有很多疑义。其第一个理由无非是“所有权神圣”的翻版。所有权不受限制的理想从来没有彻底的变为现实,并且,该理想的光辉也在民法由权利本位向社会本位过渡的大潮中逐渐黯淡;其第三、五、六之理由都可以由细化法律规定、提高法律可操作性来解决。并且道德风险可能存在的理由,反映出出租人置承租人利益于不顾的行为倾向,更从反面支持了优先购买权存在的必要性。其第二个理由合理成分最多。应该承认,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存在的确有损交易速度,导致出卖人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实现。其第四个理由直接为赞成者第一个理由所反驳。其实,反对声音中最具合理性成分的当属第二个理由——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存在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交易速度,导致出卖人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得以实现,并可能会阻碍出卖物落入最有效率的使用者之手。但是出卖人因出租出卖物已经享有过利益,在出卖之时,对其出卖条件加以适当限制,确不为过;在“同等条件”作用下,对物使用最有效率者会通过提高买价的方式来确保获得买卖物——虽然也会有些周折。而优先购买权对交易速度的些微妨碍,与它存在的两大合理性相比,也就变得可以容忍了。并且,后文还将论述,此问题可以通过正确决定优先购买权的效力而得到缓和。
(三)优先购买权的效力
笔者浅见:效力问题是一个法政策的选择问题。法政策因应现实需要,在衡量各种情势之轻重缓急之后,作出赋予某项权利何种效力的决定。这项权利被法政策确定效力后,就需要在法律的概念体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个寻找过程便是其性质确定的过程。所以,整个过程便是:现实对法政策提要求,法政策对某权利定效力,而我们则根据其效力注解出其性质。虽然高明的法学家会在运用法政策对权利赋效的同时,已经在考虑该权利赋效后在法律概念体系中的位置归属问题,但无论如何,不是先确定某项权利性质以后再考虑对其赋予什么样的效力。如果我们能够先确定某一权利在法律概念体系中的位置归属,而后确定其效力,那只是因为前人已将二者的对应关系彻底确定,所以我们可以来回逡巡而畅通无阻。如果对某项权利的性质存在重大争论,那么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先看看现实对该权利的效力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而从当前他国或地区的立法例来看,既有物权效力的优先购买权,也有债权效力的优先购买权[18]。“所谓物权的先买权,即具有物权的效力之先买权是也。物权的效力可以对抗任何人,故此种先买权之效力较强,不仅于当事人之间,可以主张;对于第三人亦可主张,亦即具有对世效力。所谓债权的先买权,即仅有债权的效力之先买权是也。债权的效力,只能于当事人间主张,不能对抗第三人,故此种先买权之效力较弱,亦仅有对人的效力。”[19]由此至少可以推得,现实生活对优先购买权的效力要求不是单一的,那么,我们在考虑赋予一项效力不明或效力尚有争论的优先购买权以何种效力的时候,就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笼而统之的加以确定,而必须结合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我国台湾地区,其“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上承租人之优先购买权被赋予了物权效力,而其他如依“土地法”而成立的优先购买权等则被赋予了债权效力。[20]
(四)优先购买权的性质
如前所述,优先购买权可以分为约定优先购买权和法定优先购买权两大类。对优先购买权进行定性是否要在这个分类下分别进行?有人明确否定:法定优先承买权和约定优先承买权之成立方式虽有不同,但基本性质应无差异,故关于其法律性质,应为统一解释。[21]约定也好,法定也罢,都只是优先购买权产生的原因而已,它们不会对优先购买权的性质进行不同塑造。这和解除权本身的性质不会因其产生原因是法定或是约定而生差异是一个道理。
在德国民法学者拉伦茨看来,对某个法律概念进行定性其实是将该概念纳入法律“(外部)体系”的一种活动,属于法律上的“构想”。在相关论述中,他指出:“‘构想’一词以下只用以描述下列活动:将法律中发现的一项规整,或交易中发展出来的一种契约模式(而不是某具体个别的契约),如此的安排入(部分)体系之中,借以产生一种无矛盾的脉络关系,并使之能与其他规整相互比较,以清楚显示其同异之处。”他还认为:构想活动中,“追寻案件解答反居次要地位,构想首先关心的倒不是个案的解决,毋宁更关切促成此脉络的思想纲领,因此,仅因借此获致的规范适用结论,其亦可以其他方式取得,这并不足以使一种‘成功的’构想丧失价值。”按照这个思路,他对优先购买权的性质进行了“构想”:法律规定:“先买权以向义务人为意思表示之方式行使之”(民法典第五〇五条第一项第一句)。同条第二项又进一步规定:“权利人与义务人间之买卖,因先买权之行使而成立,其条款与义务人及第三人间所约定者同。”此效果无疑正是行使先买之权利,借意思表示所拟获致者。因此,自然会联想到,将表示解为取向于成立买卖契约的意思表示,将先买权解为可以借意思表示创设此法效果的权利。借单方的意思表示创设法律关系(此处即买卖关系)的权利,通常可归属“形成权”一类。因此,先买权就被界定为一种形成权,然而,仅此尚不能推得其他结论,因为并无可一般的适用于全部形成权的法条。具体言之,于此涉及的是附条件的形成权;其行使的条件是:义务人与第三人就先买权的客体缔结买卖契约(民法典第五〇四条)。如此视之为一种附条件的形成权,并无任何可虑之处。[22]
有学者提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期待权。[23] “期待权”最早由德国学者提出。几个世纪以来,学者对期待权“虽有若干共同之基本认识,但于细节方面,仍多争论”。王泽鉴先生通过“观察判例学说上所承认各类期待权之性质,分析其共同特征”,得出了“所谓期待权者,系指因具备取得权利之部分要件,受法律保护,具有权利性质之法律地位”的结论。[24]王利明先生认为:“所谓期待权,是指一种将来可能取得权利的权利,其权利系寄托在将来可能取得的权利上。期待权的法律性质即决定于将来可能取得权利的法律性质。”[25]可以看出,期待权是“一种取得权利的权利”。学者指出:“约定承受权于契约订立时,随即发生,实无疑问。至于法定优先承买权……系于耕地租赁契约成立时,随即发生,而于出租人出卖或出典耕地时得为行使,学说判例均同此见解。”[26]如此看来,优先购买权随出租、出典等法律行为的成立就“形容完备”的产生了,实在没有为期待权预留存在时空。
期刊发表网 另有学者认为优先购买权是一种附强制缔约义务的买卖契约订立请求权。强制缔约,又称为强制契约、契约强制、契约缔结之强制或强制合同,是指个人或企业负有应相对人请求,与其订立合同的义务,即对相对人之要约,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拒绝承诺。在合同自由原则之下,当事人既享有决定合同内容、形式等自由,也享有缔约自由以及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即当事人可以依其自主意思决定是否订阅以及与谁订约。但是,在强制缔约制度中,由于受要约人负有强制缔约义务,必须作出承诺,因此,其缔约自由受到了相当的限制,而且,当特定要约人发出要约以后,受要约人无正当理由不得拒绝与之订约,因此其选择相对人的自由也受到限制,如承运人必须对旅客或者托运人的要约进行承诺,从而既使其丧失了缔约自由,也使其丧失了选择相对人的自由。根据违反强制缔约义务的后果的不同,强制缔约可以被区分为直接的强制缔约与间接的强制缔约两个基本类型。对直接的强制缔约而言,当负有缔约义务的一方不接受他方的要约时,要约人得诉请公权力介入,强制受要约人为承诺的意思表示。承租人的先买权可以划入直接的强制缔约之中。因此,依照附强制缔约义务的请求权说,将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视为直接强制缔约的一种,在出租人违法此义务将租赁物出卖给第三人的情形中,承租人可以诉请公权力介入,强迫出租人对其作出承诺的意思表示。[27]此种观点下的附强制缔约义务的买卖契约订立请求权在法的效力上和形成权比较接近。但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强制缔约一般存在的领域为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领域,优先购买权与此领域相差实在太远;其次,以此理论,“买卖契约之成立,尚须义务人之同意,论其实质,无异于要约,因此义务人得予拒绝,与一般买卖契约之成立,并无区别,不能合理说明优先承买权的本质。”[28]结合优先购买权的效力来看,强制缔约理论更有不周延的地方——它解释不了具有物权效力的优先购买权。来看具体例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这条规定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出租人与他人缔结的买卖合同被宣告无效后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问题。此时,有两个选择,要么承租人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要么房屋所有人重新取得房屋所有权。如果法政策赋予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以物权效力,那么承租人就应该直接取得房屋所有权。但承租人是基于什么而取得所有权呢?按照附强制缔约的买卖契约订立请求权理论,承租人发出请求(要约),房屋所有人承诺,在承租人和所有人间成立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合同。如此,承租人取得所有权还是基于买卖合同这一法律行为。而从理论上讲,如果是买卖契约的话,那么所有人还是可以违约的,仍然可以出售该房屋给其他人,而赔偿承租人的损失。这样就与该优先购买权的物权效力相矛盾。
二、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如何?我国《合同法》第230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可以看出,《合同法》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3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此项规定看似赋予了房屋承租人的优先优先购买权以物权效力,可它没有解决宣告无效后,房屋所有权的归属问题。如果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被赋予物权效力,在中国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的背景下,就应该是让承租人“请求法院宣告该买卖合同无效”的同时,基于自己单方意思表示(物权性形成权),依“同等条件”直接获得该房屋的所有权[29];如果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被赋予了债权效力,那么房屋承租人就不能宣告人家的买卖合同无效,他只能基于自己单方意思表示(债权性形成权),依“同等条件”直接在自己和出租人之间形成买卖该房的合同,然后要求出租人承担债务不能履行的合同责任。所以,这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规定带来了很多实践问题[30],也引起了人们的对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效力的诸多揣测。
本文前已述及,我们在考虑赋予一项效力不明或效力尚有争论的优先购买权以何种效力的时候,不能用一刀切的方式笼而统之的加以确定,而必须结合现实,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国台湾地区“最高法院”认为:“土地法”上之优先购买权,仅具有债权之效力,故耕地所有权已移转于他人者,不得对于承买耕地之他人,主张优先承买该地,仅能对于出租人,请求损害赔偿。而“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上规定的耕地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则被公认具有物权效力。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别,实在是因为后者要贯彻的扶植自耕农的社会政策比前者待贯彻的保护作为弱者的承租人的社会政策来的更急迫、更紧要。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赋予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以什么样的效力呢?笔者认为,应该赋予其债权效力。理由在于:
(1)如果说在房屋租赁和买卖市场还没有充分发育的时代,承租人因不能获得其承租房屋的所有权而极有可能会面临流离失所、无处栖身的窘迫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在房屋租赁、出售广告铺天盖地、租赁小传单爬满天桥栏杆的今天的确不太可能出现了。房屋所有人侵犯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固然会因推翻承租人基于承租房建立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关系而致承租人受有损失,但是这个损失完全可以通过由出租人承担违约责任加以货币化赔偿来进行弥补。再考虑到“买卖不破租赁”的规则,法律实在没有必要确保房屋承租人必须获得其承租房屋的所有权。
(2)赋予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以物权效力,对房屋所有人过于苛刻。学者在反对继续保留优先购买权时曾经使用过这个理由。笔者反对以此理由来否定优先购买权的存在价值,但认为此理由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不能赋予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物权效力。急于出售房屋的出租人真的可能在等待承租人决定是否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时间段里错失良机(比如,第三人不愿意等待)。在出租人过了此村,难寻他店的时候,处于完全主动地位的承租人会作出什么样的决定,真的让出租人心里发虚。而如果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仅具债权效力,那么,出租人可以在比较机会成本(是先出手房屋而承担违约责任还是等待优先购买权人的意思表示)之后,作出一个判断。还应看到,有时候,房屋的买卖并不会使房屋所有人与该房屋彻底脱离干系,如某大楼的所有人只出卖由他人承租的该楼部分楼层。或许承租人对该楼层的使用方式早已给出租人带来双方在订立租赁合同时并未充分预见的不利益,如承租人籍己承包的楼层开店设铺,导致该楼往来人员过于稠密、或承租人所经营之项目正与所有人形成利益竞争等。此种情形之下,出租人更愿意在承担违约责后送走承租人。但刚性的物权效力却会让房屋所有人永远处于“请神容易送神难”的被动境地,而这极有可能在无形中形成房屋租赁交易壁垒、提高房屋租赁交易成本。有人会说,房屋所有人在租赁期内不卖房屋不就可以解脱吗?可问题是这又会让房屋所有人承担房屋价钱历时下跌的巨大风险。更应注意,承租人是弱者的推定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尤其是在租赁形态纷繁复杂的今天(比如财大气粗的公司租用一个写字楼),店大欺客、客大欺店的辨正关系要求法律在结合现实情形产生一个基本判断、形成一个基本保护倾向的同时,留些柔性,保证自己适用的公平。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若被赋予物权效力则太嫌刚硬,真的不如赋予欺债权效力更显平衡。
(3)赋予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以物权效力,也不一定对承租人有利。最为典型的情形是:租赁关系仍在存续,房屋所有人(出租人)将房屋卖于第三人却不履行自己对承租人的通知义务。待不知情的承租人经多方努力于他处购得房屋之后,出租人方将租赁房屋出卖的情况告诉承租人。在这里,物权效力的优先购买权可能无法保护承租人的利益——已在他处购房的承租人即使经由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把租赁房屋的所有权变动到自己名下也可能会蒙受重大不利益,因为承租人可能并不需要两套住房。法律在此何为?回过头来看,债权效力的优先购买权则可以让承租人先在自己和房屋所有人之间成立一个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买卖合同,进而要求房屋所有人负履行不能的违约责任。
(4)反对赋予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以物权效力,最有力的理由是保护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某项权利是否可以具备物权性,取得对世效力,很重要的一点是看它是否具备公示性。权利具备了公示性,方能对抗第三人。否则,会致使财产的买方人人自危,严重损害交易安全。我们来看优先购买权是否具备了公示性。就目前法律所能找到的公示方法,无非两种,一是“占有”,二是“登记”。以“占有”来作为一项可以先于他人购买房屋这一不动产,显然过于草率。那就靠“登记”了。但在我国,除了极少数城市外,房屋租赁合同是不需要登记公示的。[31]有人主张,法定优先购买权,都应该具有物权性效力,其理由或为:“在法定先买权,并不须为预告登记,而其权利本身已具有预告登记之效力。”[32]或为法定优先购买权均基于某项特殊的社会、经济政策而设立,如不赋予其物权效力,恐难达致该政策之目的。所以法律如果“仅规定先买权,而未明文规定其物权的效力者,解释上亦应予以物权的效力。”[33]但这两个理由都经不起推敲。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都具有预告登记的效力吗?法律明确规定保护债权——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34],那是否意味所有债权都有预告登记之效力,都被赋予了对抗效力?至于第二项理由,笔者前面已经论述过了,赋予某项权利何种效力都是法政策综合考虑当前各种情势轻重缓急(包括认清各项社会、经济政策)之后作出的决断和安排,不能依某项权利是基于某项政策而设就推出其有物权效力。关键还是要看由现实决定的该项政策的紧迫性、重要性。如果说保护房屋承租人也是一项基本经济或社会政策,那么该政策的紧迫性、重要性,本文已在上面分析过了。
三、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
我国合同法第230条的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据此,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须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二是须承租人以“同等条件”表示购买。另外,根据形成权的一般理论和各国立法实践,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还应该在一定的期限内进行。在此需要先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出租人的通知是不是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有人认为出租人未履行通知义务是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35],有人则认为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是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36]笔者认为不能将出租人是否履行通知义务作为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如果出租人不履行通知义务是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那么势必造成出租人一旦履行通知义务,承租人就不能再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情况;如果出租人履行通知义务是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条件,那么在出租人不为通知,承租人自行得知出租人出卖信息的情况下,承租人同样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很显然,这两种情况对承租人来讲都是不公平的。所以出租人的通知不能作为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条件。
下面来具体分析房屋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三个条件。
(一)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
期刊发表网 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即是与他人进行就租赁房屋进行买卖。何谓“买卖”?“买卖,谓当事人约定一方转移财产权于他方,他方支付价金之契约。”[37]我国《合同法》第130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看似明了的买卖概念,在现实中却变得复杂难辨——大量“视为出卖”的规定让人挠头。《北京市房屋买卖管理暂行规定》里面的“房屋买卖”包括房屋的有偿转让、房屋产权的交换、以房屋作价投资、以自有房屋作价与他人合作扩建、改建房屋等情况;而《广州市房地产交易管理办法》亦将“以房地产出资,并已转为合资企业拥有的;以土地使用权与他人合作开发房地产,并以产权分成的;以房地产作价入股的;以房地产抵债的;收购、合并或分立企业时,房地产转移为新的权利人的等情形视为出卖。需要解答的问题是:这些“视为买卖”的情形下,房屋承租人能否行使优先购买权?有学者认为,对于这些“视为出卖”的情况,应否允许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需区分具体情况来处理,不能一概而论。首先,在房屋所有人以房屋的所有权出资、因企业的收购、合并或者分立而变更房屋所有人、以自有房屋作价与他人合作扩建、改建房屋的情况下,由于房屋所有人的目的并不在于通过出让房屋所有权而取得价金,而是具有获取房屋价金之外的其他目的,因此这些情形即使视为房屋的“出售”,承租人也不可能具备第三人所提供的“同等条件”,从而无法行使优先购买权。其次,在出租人决定进行房屋产权的交换时,因出租人之目的在于获得第三人的房屋所有权,而第三人所提供的房屋,就其大小、位置、环境等综合情况衡量,无疑是独一无二的,不会存在“同等条件”,所以承租人也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不过,如果第三人所提供交换的并不是房屋,而是其他具有替代性的物品,那么只要承租人能够提供同样内容的给付,则仍然可以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最后,在出租人以房屋抵债的情况下,因其目的在于通过房屋所有权的转移而代替金钱的给付,从这个角度说,与房屋买卖并无不同,所以应当允许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在这方面,《澳门民法典》第1308条关于共有人以其份额向第三人作代物清偿时,其他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的规定,可资参照。[38]上述看法有很大的合理性,但笔者也不完全赞同。笔者认为:纯粹意义上的房屋出卖(即出售房屋所有权,换取价金),是“关于交易之基本的契约”[39],也应该是出租人所能为的一种基本交易行为。从理论上讲,房屋所有人通过等价交换后,所获得的价金会与其房屋价值大体相当,不会获得额外暴利。而上述“视为买卖”的很多行为都是一种以房屋价值进行投资的行为(交换房屋产权的“互易”除外)。而投资行为,相对于纯粹意义上的买卖行为来讲,是一种更为高级的、出卖人享有更大自由度且可以期待获取超额利润的行为。法律对出租人的基本交易行为(纯粹意义上的买卖),尚且忍心加以限制(承租人可以优先购买权),为何反倒不能对投资行为加以限制呢?举重以明轻,故一般来讲,上述“视为买卖”的情形下,承租人皆应有优先购买权。
现在来探讨拍卖的情况下,承租人是否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根据《法国民法典》第815—15条和《瑞士民法典》第681条的规定,在拍卖的情况下,权利人仍然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在我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以下简称为《拍卖法》)第3条的规定,拍卖乃是以公开竞价的形式,将特定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转让给最高应价者的买卖方式。可见,拍卖虽然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法律设有特别规则的交易方式,但其含义尚未逸出“买卖”的文义范围之外。因此,从解释论的角度来说,对《合同法》第230条所规定的“出卖”一词进行文义解释的结果,并不能将拍卖排除在外,也就是说,在房屋拍卖的情况下,承租人仍然有权行使优先购买权。[40]杨与龄先生也认为:“强制拍卖,亦为买卖之一种,自不影响优先承买权人之权利……故不动产经拍定或交债权人承受时,执行法院知有优先承受权利人者,得依法通知其于法定期限内表示愿否优先承受。无法定期限者,则应在执行法院所定期限内行使优先承买权。优先承买权人于接到通知后,逾期未表示者,其优先权视为放弃,执行法院得交由拍定人承买。”[41]但也有不同看法——拍卖虽然属于买卖的一种方式,但毕竟法律设有特别规定;它既然以“价高者得”为原则,当不会存在两个竞买人以相同的报价而分别成交的问题。在拍卖的情况下,如果他人拍卖成交后再允许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应买之人势必锐减,卖价难免偏低,一方面不利于债权人及拍卖物之所有人,他方面也不免造成偏惠优先购买权人的结果。[42]而且还会影响拍卖行为的公信力。所以,就房屋拍卖而言,未来立法不应允许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43]笔者认为拍卖因其设计精巧(如有拍卖底价,竞买程序等),一般能给予出卖人的利益要高于普通买卖。再依举重明轻之理,自应允许房屋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话说回来,反对承租人于拍卖情形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理由同样可以用来反对承租人于普通买卖情形行使优先购买权——第三人担心自己与出租人的辛苦谈判到头来只为承租人“做嫁衣裳”,从而“应买之人势必锐减,卖价难免偏低”。法律容忍了普通买卖中这一低效率情形的发生可能,亦可以容忍拍卖中的同样可能。所以,2005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6条第一款规定:“拍卖过程中,有最高应价时,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表示以该最高价买受,如无更高应价,则拍归优先购买权人;如有更高应价,而优先购买权人不作表示的,则拍归该应价最高的竞买人。”
还有几种情况需要提到:
(1)赠与、遗赠、继承而使租赁房屋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的情况下,因为上述行为皆为无偿法律行为,根本无价额可言,出租人无因此而获得意外利益的可能[44],不在“出卖”的文义范围之内,故而承租人不得行使优先购买权,至为显然。在混合赠与的情况下,虽兼有买卖和赠与的因素,但究其实质仍以赠与的性质为主,它更多地考虑到出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人身信任关系,与纯粹的买卖终究不同,故于此情形承租人亦不得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
(2)按照《德国民法典》第570b条之(1)的规定,如果出租人将住房出卖给其家庭成员、家属或其法定继承人的,则承租人不得行使优先购买权。这种做法可资赞同,因为家庭成员之间的房屋买卖,不免具有浓厚的人身色彩,与纯粹的买卖关系终究有所不同。我国《合同法》虽无类似规定,但在操作上不妨采取同样的解释。[45]
(3)互易。作为古老的以物物交易方式在现代的延续,互易虽然为法律所允许准用关于买卖的规定,但其与买卖仍有较大的不同。通过互易,出租人获得的是非代替物,这就使得承租人无法行使先买权。另外,买卖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比较单纯的注重利益的交换,而互易则重在特定物之交换,当事人往往希望通过物之交换获得其在市场中难以买到的特定物,即使在单纯的金钱价值上受有损害也在所不惜。在不动产领域尤为如此。例如,房屋主人为了摆脱现居的生活环境,宁愿以牺牲部分住房面积为代价与另一面积稍小的房屋互易,而搬迁至另一完全陌生的环境之中。在这种情形下中,房屋出租人便不能行使先买权。[46]
(二)同等条件
期刊发表网 同等条件是对房屋承租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限制。有学者阐述了作出此种限制的意义:这首先尊重了作为出卖人的所有人的所有权,不至于因优先购买权的行使,使出卖人的利益遭受损失。同时,表明确立优先购买权并没有剥夺其他人的购买机会。如果不能提供同等条件,则按价高者得的市场原则决定物的归属,因此不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47]
但对于同等条件的具体内涵是什么的问题,大家看法各异。《德国民法典》第505条第2款规定:“一经行使先买权,先买权人与先卖义务人之间的买卖即按照先卖义务人与第三人约定的相同的条款而成立。”[48]有人主张,应当借鉴德国法的上述经验,采用“相同条款”作为先买权人行使权利的条件。但这种所谓的“绝对等同说”关于“同等条件”的内容,在适用中过于苛刻,先买权在现实中恐有不能实现之虞。[49]而事实上,《德国民法典》在505条第2款规定之后,也用下列条款对“相同条款”进行了缓和:
——507条:第三人对合同中先买权人不能履行的从给付负有义务的,先买权人可以支付从给付的价金代替给付。从给付不能以金钱估价时,不得行使先买权;但无此给付,与第三人的合同亦能成立,对此种给付的约定不予考虑。
——509条(延期支付价金)
(1) 如果在合同中允许第三人延期支付价金,先买权人只能在为延期支付的价金提供担保时,始得请求延期付款。
(2) 土地为先买权标的物的,只有在约定就土地上为延期付款设定抵押权,或者因抵充部分价金而承担在该土地上设有抵押权的债务时,才无需提供担保。注册的船舶或者建造中的船舶为先买权标的物的,准用上述规定。[50]
现在让我们来具体分析同等条件的构成问题。
作为买卖合同的一种,房屋买卖行为必然要包含买卖标的物和价金两大条款。房屋买卖的条件是否等同,首先要看标的物和价金两大条款是否等同。
(1)标的物条款。有关优先购买权的争讼中,当事人争讼对象就是同一房屋,所以标的物条款本不会产生是否等同的疑问。但是,在高层建筑非常普遍的今天,此类问题便产生了。本案即是一个例证。设想一幢大楼的所有者欲整体出售该楼,但该楼某个房间单元又已被某承租人承租,第三人购得该幢大楼后,某承租人站出来主张对自己所租房间的优先购买权——这里,承租人主张优先购买的标的和出租人出卖的标的并不同一,前者为后者所包含——此时,是否就可以承租人和第三人买卖标的本就不同,根本不符合“同等条件”而对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不予理睬呢?不予理睬?实难讲通,小小承租人在巍巍楼宇前更像“弱者”;推翻其以承租房屋为基础建立起的各种关系同样会给他伤害;给予理睬?欲购整幢大楼的第三人允许自己的“领地”上存在“国中之国”吗?若因此导致第三人拂袖离去,所有人将会遭受重大损失。回顾本文主张的赋予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以债权效力的观点,此难题便会迎刃而解。依然保护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第三人同意购买楼房除该承租房屋以外的所有部分,满足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自然皆大欢喜;第三人不愿作此分割的,所有人出卖整幢楼房于第三人后,承担对承租人的违约责任,赔偿其损失即可。
(2)价金条款。首先是价金数额等同,即承租人允诺支付的价款数额应等同于第三人在合同中允诺支付的价款。其次,关于价款的支付方式,也应等同于第三人允诺的方式。例如,第三人允诺一次付清者,承租人不得主张分期支付。不过,如果出租人允许第三人分期付款,则承租人除非为出租人提供了充分而适当的反保,否则不能请求分期付款。《德国民法典》第509条对此设有明文规定,可资参照。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每个人的信用及支付能力未尽相同,出租人信赖第三人的支付能力,承租人却未必能赢得同样的信赖。[51]
除开上述两大条款外,“同等条件”是否也包含其他交易条件的等同?有学者根据《德国民法典》第507条的规定认为第三人允诺对出租人负担从给付义务的,除非该从给付义务可以用金钱作价,或无此从给付义务出租人与第三人的合同亦能成立,否则承租人不得行使优先购买权。[52]笔者表示赞同。据此,先看从给付是否为出租人和第三人成立买卖契约所必需,如不是必需,则在判断同等条件时不考虑该从给付约定;如是必须,再看该从给付是否可用金钱来衡量。如果该从给付不可用金钱来衡量,承租人就不能行使优先购买权;反之,承租人可在用金钱代替该从给付后行使优先购买权。当然,在确定哪些从给付为成立契约所必需时需要法官丰富的经验和充足的智慧,这不是法律条文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
综上,笔者认为,确定“同等条件”需要通盘考虑上述因素后作出决定,而不能单考察某一个条件(如价金数额相同)便做定论。另外,依举重明轻之原则,如果承租人提供的条件优于第三人提供的条件,承租人自然可以行使优先购买权。
(三)合理期限
期刊发表网 学者普遍认为,形成权不是请求权,因而它不受诉讼实效的限制。但形成权持续时间太长会产生不良后果,并且形成权因权利人的不行使将会使形成权的效力减弱。因此,形成权在一定的时期内不行使,将导致其消灭。此一期间被称为除斥期间。[53]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作为一种形成权,理所当然的应该适用除斥期间。如此,才能发挥优先购买权的积极作用,即首先有利于民事主体在特定买卖关系中取得自己所需要的财产,以满足其工组和生活的特殊需要;其次有利于发挥物的效用,以达到物尽其用;再次有利于交易安全,维护正常的财产流通秩序和社会安定。[54]
各国立法对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除斥期间规定不一。德国民法典第510条规定:“(1)先卖义务人应将其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的内容,立即通知先买权人。第三人的通知可以代替先卖义务人的通知。(2)土地的优先权只能在收到通知后两个月内行使,其他标的物的先买权只能在收到通知后一个星期内行使。对行使先买权约定有期限的,以约定期限代替法定期限。”[55]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426条之二第二款规定:“前项情形,出卖人应将出卖条件以书面通知优先承买权人。优先承买权人于通知达到后十日内未以书面表示承买者,视为放弃”。[56]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国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18条规定,“出租人出卖出租房屋,应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权;出租人未按此规定出卖房屋的,承租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宣告该房屋买卖无效”,国务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11条也规定,“房屋所有人出卖出租房屋,须提前三个月通知承租人。在同等条件下承租人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可以看出,我们国家的法律对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除斥期间的规定方式和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规定是有区别的:我国是从出租人的角度规定出租人应于出卖标的物前的某一段时间通知承租人,他国或地区是从承租人的角度规定承租人应于受到通知后的一定时间内为购买的意思表示。有学者认为:“这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但其欲达致的目标却是相同的。”[57]笔者对此持不同看法。首先需要明白:该除斥期间的规定是适用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的,既然如此,立法的表述形式应该是房屋承租人在哪段时间内行使优先购买权及逾期的后果,而不是规定他人应该提前一段时间履行通知义务。实践中,我国“提前三个月”的立法模式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第一,“出卖出租房屋”究竟是指出卖意向还是出卖要约还是出卖契约订立?第二,“提前三个月”的立法技巧让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那么容易“受伤”,并且让其“伤势”呈现“轻微伤”、“轻伤”、“重伤”等多种状态——出租人提前2个月通知给承租人造成的伤害可能是“轻微伤”;提前1个月造成的伤害可能是“轻伤”;仅提前10天造成的伤害是“重伤”……法律何苦自寻烦恼,将自己推入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漩涡?相形之下,从承租人的角度规定承租人应于受到通知后的一定时间内为购买的意思表示,显得干净、明快——出租人通知了,除斥期间的起算点就确定了;出租人不通知,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就受到了侵犯。
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出卖人不履行通知义务,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的除斥期间从何起算?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合同法》第55条的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其撤销权消灭——将此情形下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除斥期间的起算点规定为“房屋承租人知道或应当知道优先购买权行使事由时”,除斥期间的长度为一年。[58]
四、结论
期刊发表网 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确有存在之必要。但对其赋予何种效力则必须结合中国现实国情综合思量之后再予确定。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应该赋予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以债权效力并认为它是形成权之一种。一旦明确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的效力和性质,探讨它的行使条件就比较轻松了——尤其是本案所关涉的房屋承租人所承租的房屋与出租人卖与第三人的房屋是否需要完全同一的问题就比较容易得到解决。回到本案,我们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原告对自己承租的浩达大厦内的380平方米的房屋享有优先购买权。在此前提下,对案件的分析思路恐怕应该是这样的:在浩达通商经贸公司没有履行通知义务从而侵犯原告优先购买权的情况下,原告可以经由优先购买权的行使,基于自己单方意思表示(债权性形成权),依“同等条件”直接在自己和浩达通商经贸公司之间形成买卖原告承租的380平方米房屋的合同,然后要求出租人承担债务不能履行的合同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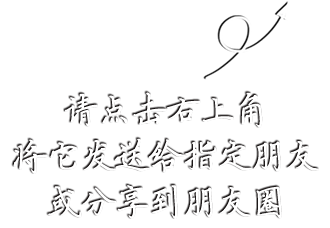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