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学文学院,山西,太原 030000)
摘 要:母女关系是美国女作家玛莎·诺曼关注的重要命题,《晚安,妈妈》作为玛莎·诺曼的代表作,聚焦于父权社会中女性的生存困境及心理感受。本文对剧中女性生存困境以及身份重构过程进行剖析,可以看出《晚安,妈妈》为当代女性构建主体自我提供了重要的文化途径。
关键词:生存困境;身份重建;女性主义
《晚安,妈妈》这部戏剧以母女二人之间的对话展开,严格遵守戏剧的“三一律”原则,即时间、地点、行动的统一。
时间从晚上八点多到深夜,故事发生在家中,围绕杰茜要自杀的线索展开故事情节。在传统的线性表现形式之下,《晚安,妈妈》的颠覆性也非常显著,首先反映在剧中的人物形象设置上,故事的主要人物是两个女人,男性形象可以说这里是缺席的(仅出现在母女二人的对话中);其次,两个女人的关系实质上是母女之间意志的冲突——人类原本最亲密的关系在这里被异化;最重要的是,这部剧的意义更体现在对女性的生存困境的探讨及女性主体性的重构上。
一、两位母亲的生存处境
在以父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女性的生理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女性的生活必定会局限在家庭领域,随着年龄增长,母亲身份也成为绝大部分女性的最终命运。露丝·伊利格瑞不断强调在父权文化中被边缘化的母亲,母亲为他人牺牲了自己的欲望和需要,却被男性标准排斥于社会的边缘。母亲是他者,是沉默的,无法表达自己的欲望。剧中的赛尔玛就是这样一个被边缘化、被他者化的母亲。作为妻子,丈夫拒绝和她说话,比如出门钓鱼是挂一个“钓鱼去了”的牌子挂在卧室门口,甚至至死也不愿和她道别,从而剥夺了她的话语权,她从不知道丈夫在想什么,她的一生都处于无休止的等待中。“如果从传统观念来看,作为母亲的妇女对男人代表着一种归属地”,“对于作为母亲的妇女,我们就称她为‘阉割者’”。所以说,在父权社会中,塞尔玛的话语和身份都被阉割了,被阉割了的母亲被主流文化所忽视,所遗忘,从而失去了独立的身份,对于塞尔玛来说,生活无需思考,只需继续。
而杰茜的处境也并不比她的母亲好,杰茜从小身患癫痫,四十多年来饱受病痛的折磨,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工作、生活。
面对客体化、边缘化的母亲也无法给杰茜在精神上树立正面积极的形象,“母亲自身独立身份的丧失导致女儿生存困境更加困难。”无法言说自己欲望的母亲把欲望和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女儿身上,因为杰茜的疾病,塞尔玛对杰茜的保护也格外强烈。她用谎言掩盖女儿疾病的真相,并一手安排女儿的婚姻。尽管杰茜爱自己的丈夫塞西尔,但塞西尔却不满杰茜抽烟,也不高兴她随他离开那个地方,进而出轨,并让杰茜在“抽烟”和他自己之间选择,最后还是把杰茜当“垃圾”
一样抛弃。杰茜没有工作、收入、账户和朋友,每日工作就是处理日常家务。作为母亲和妻子,杰茜与塞尔玛的处境非常相似,家庭是她们活动的主要地方,在那里她们主要扮演欲望的对象。 在长期的共处中,从母亲的经历杰茜看到自己的未来,所以她知道追随母亲的脚步不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她把人生比作坐公车,“车里很闷,很吵,你很想下车,但离你的终点站还有很远。我要下车了,即使我再坐 50 年下车,和现在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受够了。”母亲的生活状态让杰茜感到窒息,所以她决定离开,离开母亲。由于母亲没有正确的女性主体身份,女儿无法效仿母亲,她意识到跟随母亲没有前途,“如果你只是想把我塑造成另一个你,一个没有活力的你,那么我将追随父亲,一个比你有活力的人”。
杰茜转向父亲寻求主体性,但是父权体系更没法满足她这种愿望。于是我们看到剧中趋于男性化的杰茜,从衣着到习惯,甚至最后自杀也是用父亲的枪完成的。转向男性的杰茜受到各种重创,丈夫让她在他和抽烟之间做出选择,然后遗弃了她;儿子更是偏离了正常的成长轨迹,在犯罪的路上越走越远;而看似疼爱她的哥哥则完全不把她当成年人看待,肆意践踏她的隐私。由于男性是秩序的缔造者,所以话语是男性的,而所谓的女性气质,不过是根据男性的价值观念强加于女性的一套形象、特性、角色的总和。女性气质使女性失去了自我,为了具备女性气质而失去了自我,所以杰茜对于父亲的追随也以失败而告终。
二、身份重建
母亲塞尔玛面对自己他者化的境遇并非无察觉,潜意识里也没有对自己被丈夫当作“替罪羊”的角色心存不满。塞尔玛没有刻意改变自己逢迎丈夫的期待,而且“从来也没喜欢过做饭”。尽管如此,塞尔玛大部分时间还是选择了逆来顺受,被动等待。与母亲得过且过不同,杰茜选择行动,杰茜是一位与塞尔玛不一样的母亲。杰茜明白女性要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母亲,她首先得是一个独立的人。抽烟是阳性的象征,通常女性是不能参与的。但杰茜却喜欢抽烟,当丈夫让她在抽烟和他之间做选择,杰茜坚持表达自己的欲望,选择抽烟。抽烟既是杰茜对自己他者身份的抗议,也是对男性权威的挑战。杰茜的男性化衣着同样表现她的反抗。“杰茜身着长裤,黑色长毛绒衫,口袋挺深,里头装着些纸片,她耳后可能还插着一支铅笔,或在毛绒衫的一个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无论是抽烟还是穿着都体现杰茜对平等的渴望,而铅笔、钢笔更是暗示杰茜渴望拥有话语权和独立思想。面对一直关心自己的哥哥,杰茜也非常不满。无论是哥哥送的拖鞋还是对她的昵称,在杰茜看来都透着哥哥居高临下的自我优越感,令她反感。与母亲浑浑噩噩的生活相比,杰茜目标更明确,意志更坚定。 在母亲身份的认知上,杰茜与塞尔玛也很不同。传统的母亲以儿子为中心,塞尔玛也不例外。丈夫去世后,塞尔玛没了主见,家里大小事都让儿子做主。另外,从传统的母亲角色看,杰茜和塞尔玛都比较失败。塞尔玛女儿要自杀,杰茜儿子吸毒成瘾,沦为小偷,但两个母亲面对孩子的态度却截然不同。当塞尔玛听到杰茜要自杀,她很自责,觉得自己失责毁了杰茜的一生。但杰茜却不把儿子的犯罪与自己绑架在一起。杰茜将儿子视为独立个体,儿子犯罪是他自作自受,他得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杰茜比塞尔玛更有身份的疆界意识,明白母亲与孩子之间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个体。
基于这样的认知,重构她与母亲的关系是杰茜重获自主性的重要一环。杰茜深知,只有冲破与母亲原始的共生关系,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母亲塞尔玛从小就对杰茜严加控制,从隐瞒病情到一手包办她的婚姻,再到杰茜婚姻失败收留 她甚至规划女儿的生活,无一不体现出母亲对杰茜自我边界的侵犯。塞尔玛对杰茜的“吞噬”进一步加深了杰茜“无我”感。面对杰茜的自杀,母亲苦苦相劝,一再强调杰茜是她的孩子,而杰茜却不停反驳她不是母亲的“私有财产”,而是一个独立的成人。“如果自杀是我永远摆脱您的唯一办法那又怎么样?如果是这样的又怎么样?我照样能自杀。”
塞尔玛终于明白,孩子虽来源于母亲,与母亲血脉相连,但孩子又是一个独立的个体,独立于母亲,孩子有属于自己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思想。
总之,《晚安,妈妈》这部剧是关于母亲身份、又或曰女性身份主体性建构以及自主意识的唤醒。母亲角色一直是西方戏剧创作传统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之一,从古希腊悲剧一直延续到现代社会中的家庭剧。长期以来,母亲角色常常以家庭成员的欲望对象而存在,但这一形象在诺曼的作品中遭到挑战。女儿杰茜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重构母女关系,也重塑了自我,不仅将母亲从自责、悔恨中解放出来,也给予母亲重新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实现精神上的蜕变。同时也为当代女性构建主体自我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路径。
参考文献:
[1] 张京媛 .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 北京 :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2][ 法 ] 西蒙娜·德·波伏瓦著 . 陶铁柱译 . 第二性 [M].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3] 张玫玫 . 露丝·伊利格瑞的女性主体性建构之维 [J]. 国外文学 ,2009,29(02):11-18.
[4] 刘秀玉 . 从《晚安 , 妈妈》看玛莎·诺曼的女性主义戏剧创作 [J]. 辽宁大学学报 (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8(03):59-62.
[5] 贺安芳 . 母女关系视角下的玛莎·诺曼作品研究 [J]. 宁波大学学报 ( 人文科学版),2013,26(03):32-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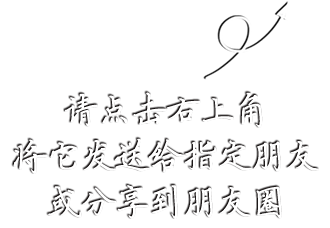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