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我”到“主体——“社群主义文化批判
2010年12月06日 15:15 作者:职称论文
论文网(www.lunww.com )是期刊推广、论文发表、论文写作指导的正规代理机构,我们与4、5百家省级、国家级、核心期刊有合作,我们合作的期刊都是万方、维普、中国知网、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收录的正规期刊。合作的期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可查,详情可来电0519-83865052,或者QQ:85782530咨询。个人主义、相对主义①在现代西方社会的大众文化和大众心理中占据着统治地位,导致了意义的丧失、工具理性猖撅和自由的偏颇。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社群主义”②对个人自由以及由此形成的个人权利进行了强烈批判。它认为,个人主义将个人自由“原子”化、将国家或社会工具化,应该取消“原子论”( Atomi sm)意义上的“个人自由”,代之以“社会背景”、“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有时可以简称为“文化背景”或“道德背景”),才能解决西方社会大众文化与大众心理的隐忧。然而,“社群主义”的这种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导致了“自我”的隐蔽。
“社群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加拿大政治哲学家泰勒(Charles Taylor)认为,个人主义只知有“我的”而不知有“我”,将“我”看作产生于“虚无”(Ex-nihilo)的东西,然后谈“个人自由”,使自由没有必然的意义。泰勒的这一击,实质上,把个人自由从描述性理解逼到内在的规范性要求上。在《现代性之隐忧》(The Malaise of Modernity)一书中,泰勒针对现代人并没有“生活在我们应当的生活之中”的现状指出,“我”应是“追寻着”(Seeking)的本质的“我”,即自我限定(Self-defined )的“我”,因而,“我”也就能够被伸展为真实的“我”。而“个人自由”把个人(即“我”)看作是独立于社会之外的自我满足( Self-sufficient ),必然会摧毁自由的社会。因为“它错误地坚持了个人自由主义假设背景的程度:在那里,单独的个人是社会成员,而且是忠实的社会成员,(他们)促进了一些特殊的价值,诸如:自由、个人差异。幸运的是,大多数人民在自由的社会里,并不把他们自己视为原子论的自我”。;l](PI08)0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社会动物”—人应当是由社会、历史和文化所规定的。所以,泰勒对“我”的追寻也就是社会、历史和文化对个人选择和自我规定而言的内化过程,它与哈耶克所理解的“介于理性与本能之间”的习惯、风俗是个人自由的前提这种观点,是大不一样的。因为,在哈耶克那里,“我”并没有对已有的文化背景进行自我的追寻过程。
与之相呼应,“社群主义”另一个著名代表人物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也认为,自由主义以“多元论”为背景,但是,“多元论的观念很不确切。因为它既可以很好地适用于交叉着不同的观点的有条理的对话,也可以适用于杂乱碎片的不和谐的杂烩。"} ,z]<Pia,以他的理解,个人主义的文化内涵中,只有“多”而没有“元”,应探讨“元”的意义上的“多”,才是真正的“多元”。
与麦金太尔一样,泰勒认为,正义的标准只能从各个不同的特殊社会传统和文化背景及其变迁中得以发现和确证。如果以“社群主义”的方式来理解的话,个人主义首先应以“内在”的个人主体,即在具有丰富的传统性或社会文化背景的主体意义上,去谈论自由问题。我们认为,个人主义将个人自由外在化为对个人权利的描述,缺少自由与权利之间的内在必然性,确实会导致自由于外而失之于内,因而,被誉为“自由主义大师”的柏林(IsaiahBerlin )曾有“我们为什么生活在表层”的感慨。但是,“社群主义”对“文化”、“传统”等概念的理解是模糊的,因此,他们并不能确切地寻求到真切的文化之“元”。例如,他们在举例当中涉及中国传统时说,中国人有在自己最痛恨的人家门前自杀,以示强烈抗议的习俗。也许中国古代真的有这种事例,那也只,是极个别现象,因为,从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推不出这种行为的合理性。况且,如果仅以某些传统文化为自由的前提,结果很有可能就等于没有自由。比如,印度的种性制度,至今还在有些地方延续,如果以此为标准,这些地区就没有任何个人的自由可
为此,一般的“社群主义”者都提出所谓“非自由的正义”( Non-liberal Justice)概念,以之表达自由并非人类的必须。大致说来,占据“社群主义”核心地位的“文化”(或文化传统)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文化因素能够影响权利的次序,换句话说,不同的社会权利结构是因不同的文化理解,从而导致对人们的权利要求的范围及其应得有所增减。第二,文化因素能够而且应当影响权利的正当性。例如,新加坡的民主权利结构就是家庭成员之间权利关系的放大。第三,文化因素能够提供区分政治的实践和公共机构的道德基础。这种纯粹以文化(包括社会与历史传统)为目的的正义论,我们可以称之为“极端的正义论”。因为,在很多不同的文化和传统当中,对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非自由”问题,而是“不自由”、甚至反自由的问题,“社群主义”却忽视了这个严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
按照“社群主义”的观点,既然人的主体性是由文化来决定的,那么对人的尊重,就应该转变为对·不同文化的尊重。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后,“社群主义”提出“跨文化对话”(Cross-cultural Dialogue)和政治赏识”(’The Politics of Recognition ),企图以此确立“自我”和实现“自我”。泰勒认为,以康德的自由意志而形成的自由观,只是欧洲或白人的文化观。因而,它只是对这一文化背景下的个人实现平等尊重(Equal Respect ),而没有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的个人实现平等赏识(Equal Recognition ) o这种批判的确是有道理的,比如:西方观念中的“上帝”是在世的人生或人的观念所不能企及的,所以,他们对上帝只能说“不是什么”,而不能说“是什么”,这基本上是不可知论的态度,所以其市场观念也就否定人为控制,而要求“自然化”。与之相反,我们中国人所理解的“佛”则是人生可以通过修行能够达到的某种境界,因此,我们较容易接受可知论(我们的儒家学说也同样讲求“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泰勒就是想要说明,个人主义的自由观只是欧洲或白人文化中所理解的自由,而且,这种自由观所表达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冷淡的。泰勒认为,个人主义从实质上讲只是自治意义上的程序自由主义(ProceduralLiberalism )。然而,我们应当把每一种不同文化理解为不同的价值目标,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尊重需要文化的赏识。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呢?为了确认个人之间的平等尊重,我们需要承认他人所处的文化(背景—原文缺漏)。泰勒宣称,个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就是社会地和对话地建构,同时,为了尊重人的价值,在一个国家的政体组织里,使每一个人能够持有和追求他或她自己所认同的善。但是,我们认为,“社群主义”的“跨文化对话”到底能够延展到多大范围,或到底能够进展得多深人,这与罗尔斯“多元理性论”的“交叠共识”所存在的隐患具有相似性。因为,要进行文化对话必须有一个对话立场,如果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话就会成为不可能。所以,只能站在中性的立场,那就只能是首先“离开”自己的文化背景,以人的方式来尊重他人。我们中国人所提倡的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政”为中心的“五项原则”就是这个道理。泰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也只是论证过对话的必要性与如何对话。这样一来,“社群主义”的“对话”逻辑就成了问题,深层次的对话更成为不可能。另外,以纯粹的文化对话方式很难做到平等对话,因为对话的前提是无法平等的。只有当我们中国的商品进人美国家庭的餐桌上、小孩子喜欢的玩具中、商人们的商用设备里和联邦政府办公用品之中……;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所提出的工业标准、管理方式、服务准则……等等,被普遍化或世界化,才能有美国对中国的平等对话。然而,这都很难做到。
以文化认同建构政治是“社群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的第二次浪潮。“社群主义”所设想的乌托邦是一个“异质性的文化社群”,于是,形成了“社群政治”观。“社群主义”认为,个人自由主义以个人权利占据国家政治的中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对立的根源。在现代社会,文化对话应成为核心,一切冲突与争论皆为非法。这种乌托邦指出,社群团体是一个基于地理区域之上的文化社群,或者说是一个“文化—地理”意义上的社群,也可以称之为“社区大家庭”。一个人从出生到成长,在此过程中获得身份的确立,直到长大成人,离开社群或“社区大家庭”。而社群的“政治的权威应视为在考虑发展计划时的某一个社群存在的特征”,如社群的建筑特征、促进社群里人们之间的友谊等,皆需要社群的政治权威。
当今的一些“社群主义”者共同创作了一本书,名为《心的习惯)) ( Habits of the Heart ),在这本书中,他们描述了一个以语言为基础的不同的民族文化群体。在群体里,人们分享着对社群历史的记忆为共同的利益贡献着自己。在那里,人们在面对面的私人交流过程中,被信任的情操、共同合作和利他主义所支撑—人们自觉地遵循自然法。
“社群主义”以牺牲自由为代价而直接以平等填充;代替个人主义“原子论”的是“文化原子论”;泰勒所追寻的“我”,最终被以文化、价值为目的的乌托邦模式锁闭于“文化原子”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天主教国家爱尔兰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刚满十四岁的小姑娘被暴徒强暴后不幸怀孕。这时,如果进行人工流产,以天主教教规来说,无疑是“杀婴”,然而,这个无辜的少女不做妈妈的权利又如何才能得以保障(因为她没有能力和资格)?所以,当时双方观点对立的人们,只是以沉默游行的方式表达一种文化矛盾的悲哀。所以,这样一种以文化乌托邦方式存在的群体,当这个文化乌托邦内部出现文化矛盾时,人们又何以能够从中追寻本质,追寻“自我”呢?我们并不认为波普尔有意把黑格尔的国家观称作“部落主义”是准确的,但用于描绘“社群主义”则无疑是贴切的。对泰勒本人而言,以现代人的焦虑为自我追寻的前提,同样无法获得内在的自我规定。
从某种意义上讲,“社群主义”的确暴露了现代西方社会自由与平等的内在矛盾,但它却未能合理地予以解决。因为,它以高调的“自我追寻”开始,却以低调的“自我隐蔽”结束。更有研究者尖锐地指出,“社群价值必然建立在判断人类经验共享的外在和超越的价值标准上(社群主义的跨文化对话只能导致这样一个结果—作者),……他们的价值理论必定产生一个所有依其逻辑结果而生活于其中的人的怪物”。[3]“社群主义”的这种文化乌托邦,若以人民或民族的价值、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只能是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的现代缩影。
我们应当看到,个人主义的根本教条是经过改造的、康德的“人是目的,而不仅仅以人为工具”这一“绝对命令”,而“社群主义”基本上没有触及这一问题。如果我们依据“社群主义”的“追寻”逻辑再往前追问一步:到底是谁,何以能“以人为工具”?到底是谁,何以能“以人为目的,而不仅仅以人为工具”?马克思主义的回答是:是人而不是上帝,是“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和“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的结果。因为,这个“人”处于特定社会结构和特定历史阶段之中。所以,这个“人”也是应当进行批判或自我批判的人。这种提问就是一个前提性的追问,与泰勒“去尾式”的追问—去“我的”为“我”、而仅仅确立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人,是绝不相同的,它把一个直觉问题自觉为一个辩证法的问题、把人的生活状态从描述性地理解表达为“辩证—批判”性地理解。所以,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批判,确立了人;对社会结构的批判,确立了现实的人;对历史的批判,确立了发展进程中的人;人对自我的批判,确立了实践(辩证法)即主体意义上的人,即最终确立了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这样,人才是真正主体意义上的人,也是泰勒等“社群主义”者所应当追寻的“真实性”。
如果以宗教目的论的方式来看,人是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主体地位的,人所面对的“现实”并不具有必然性,一切“现实”只是假象和偶然的.人在现实中的一切行为、活动及其所形成的思维方式必须以宗教目的论为核心‘:而“启蒙运动”划定了人与上帝的界限,这就决定了他们所理解的人只是“主动者”,即Agent,这个观念被个人主义与“社群主义”直接利用。然而,马克思主义以彻底的宗教批判开始,奠定真正意义上主体性的人(即Subject,与客观必然性相对)—自由的人。马克思指出,“在自由被埋葬的那一天,才在我们的牧师的领导下处于自由社会。},[41(P!)因此,“宗教是那些还没有获得自己或再度丧失了自己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一,j;1’1 )那么,“反对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就是反对以宗教为精神慰藉的那个世界的斗争。; }511}’人的自由存在于任何既定社会之中,但是,需要对这个既定社会中的人的异化进行批判性揭露才能获得。具体说来,随着自发分工的形成、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人的社会活动成为人作为类的异化物而存在,人类劳动的“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 51(P.!>3 l人也就丧失了目己的目的和自由—主体丧失为特定社会的“自我”。因而,人的自由并不是直接被给予的,而是现实的、历史的实践活动所形成的,即在人逐步占有人自身、占有现实生活的实践中形成的。
既然如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自由的前提是社会自由,而它又是历史地实现着的,即“每一个单独的个人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51(Pa2,,归根结底,是受物质生活条件及其历史发展制约的。在异化的社会里,“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他们从“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 (恩格斯语)。然而,这又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正如马克思所说,‘.当旧制度本身还相信而且也应当相信自己的合理性的时候,它的历史是悲剧性的”。:47cPS>只有当社会生产高度发展,“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人的实践本性得以实现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 l crno’这时,人类的自由与平等才能真正得以实现。
自由是人类实践本性的必然表达,因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也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 [4](1’1?b)这里的“自为地存在着”,即是实践的否定性,亦即实践的整体性,因为整体性同时就是否定性,并因而才能具有自由。对实践只是从伦理或道德的角度来理解,这是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到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传统模式,“社群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麦金太尔也不例外。
这是由于他们把伦理或道德视为惟一的实践行为要求而使然。马克思主义在对黑格尔实践观进行批判性改造的基础上,将实践理解为改造世界的“人的感性的活动”,而不只是单一的伦理或道德活动。所以,实践才具有全面性和整体性。同时,由实践这一特点所蕴含的否定性,是对任何现实的否定,所以,它没有、也不可能存在所谓逻辑先在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实践观的本质区别,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实践—现实地阶进”)以及由此而产生对自由的异化问题—在实践中,肯定性是对人隐匿地存在着、唯有在否定过程中人才能是显现着的存在,即人对现实(矛盾着的现实)的肯定性理解中包含着否定性的理解,亦即批判性的理解,因而,对实践着的人而言,实践必然地也就是他的自由。
所以,马克思主义对人的主体性理解不是对权利的要求或期待,而是对权利的肯定中的否定,唯其如此,人作为主体才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反过来,这样的人的自由,才能被称为主体性。当今西方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几乎都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利他主义的纯粹义务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其实,无论利他或利己,只要不导致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异化即为正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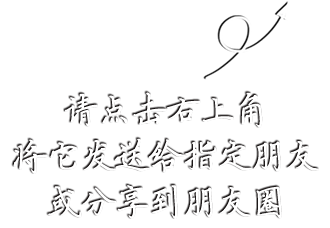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