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深深扎根于悠久的历史长河之中,在社会历史发展长河之中,有一个历史阶段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奠基阶段,这就是先秦时期。先秦诸子围绕人与自然、人与人、个体与社会的关系等一些重大问题来展开论争,并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了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在群己关系上提出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从此开启了一扇古代中国哲学价值问题探讨的大门。应当承认,先秦诸子各家在这些问题上的探讨,一开始并非十分合理,各派各家各有所偏,但经过他们激烈的论战,各派的一些继承者不断修正、完善自己的学说,吸收、融合其他各派的合理观点,最终形成了比较合理的价值原则、价值体系,即中华文化中的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统一、既尊重个性又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的群己统一原则,这也正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
先秦诸子之所以能率先提出这些重大的价值原则,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密不可分,先秦诸子能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论战,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首先,从社会性质来说,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学术上提倡百家争鸣,迎来了文化的空前繁荣。其次,这个时期由于铁器的广泛应用,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促使社会分工加剧,出现了一个知识阶层—士阶层。士阶层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学在官府”局面,大兴私人讲学之风,著书立说,创立学派,从而促使学派林立,学说各异。再次,在这一时期中华文化已经经历了长达几千年的积累,从仰韶文化,经过夏、商、周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突变时期。最后,春秋战国时期,国家四分五裂,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不同的思想可以自由地进行论争。就像庄子所说:“道术将为天下裂”。原来统一的“道术”分裂了,于是诸子百家纷纷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并就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
法学论文发表 一、人道原则和自然原则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古代哲学主要通过天人关系来探讨这一问题。在中国古代,天既被赋予自然的因素,又被赋予道德因素。儒家倡导“天人合一”,这里的“天”侧重于天的道德因素,所以,儒家教化人要做“圣人”;而道家更多强调天的自然因素,所以,道家提倡人要做“真人”。孔子说:“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他认为尧效法“天”创造出了一套制度,于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代代相传,而这一制度的核心是仁,是永远不变的,这就充分体现了儒家天人关系上的人道原则。老子用天道来与孔子的人道对立。老子提出“无为”思想,“无为”即自然。所谓“道常无为而不为”,就是说道对万物的作用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持,长而不宰”。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说人尧效法天地,而天地之道无非是自然法则。显然,道家所倡导的是自然原则。
在人与人的关系,儒墨倡导的人道原则与老庄讲的自然原则之争更为明显。儒墨讲仁爱,孔子贵仁,墨子贵兼,二人的说法不同,但都肯定了人道原则,即肯定爱的价值、人的尊严,主张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尊重,建立爱和信任关系。孔子说:“鸟兽不可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意思是说人要和人相处,必须要有爱心,要有同情心。孔子认为,行仁之方在于实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忠恕之道。墨子也主张:“兼即仁矣,义矣。”后期的墨家更明显地表达了人道原则,《墨经》里讲:“仁,爱己者,非为用己也,不若爱马者。”意思是说,真正的爱就是爱别人如同爱自己,把每个人都看成像自己一样的主体。孔墨讲人类应该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自己的能力和德性,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培养自己的理想人格。 与孔墨相对立,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意思是说自然界无所谓仁爱,圣人对百姓也不施仁爱,就像束草为狗,用作祭物,祭祀完了,就把它丢掉,根本无所谓爱憎。老子认为,培养人的理想人格,不能靠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关系,而应该复归自然。老子说:“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否认人为的重要性,认为自然就是无为,这是道家自然原则的体现。
儒墨强调人道原则,老庄侧重自然原则。先秦诸子各家在激烈的论战中既相互攻击,构建自己的学术观点,同时又相互融合、吸收其他学派的合理观点。如果任何一家将其观点绝对化,就会造成其理论向极端的方向发展。当然,这种背离是正常的,符合人类认识的发展规律。同时,这种背离是短暂的,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支流,中国古代哲学发展总的趋势是人道原则与自然原则的统一。儒家继承者荀子提出的“化性起伪”说,就是指在自然上面加上人工。后来王安石说:“礼始于天而成于人。”就是说礼义都是人在自然之上附加人工的结果,他主张“以道扰民”,“扰”就是尊重人,因其天性之自然而加以诱导。这就充分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结合。王夫之更是强调:“性日生而日成,习成而性与成。”这种成身成性,循环定性,源于自然(天性)而归于自然(德性)的习性观,进一步体现了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结合。
法学论文发表 二、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先秦儒墨重视群体利益倡导人要过社会性的生活。与儒墨相对立的是道家杨朱的“为我”、“贵己”说,道家杨朱把个人的生命与社会的利益对立起来,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不一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这显然是避世之士的主张。与儒墨讲的人道原则,提倡人要过社会生活完全不同的是,孟子批评说:“杨朱为我,是无君也。”荀子进一步发挥了儒家关于群体的理论,他指出,人要生活,要假物以为用,必须靠集体的力量。由此进而指出,为了合群,便须有一定的社会分工和分配制度,同时,还要有一定的政治法律和道德规范予以保证和约束。荀子说:“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可见,在荀子看来,礼义等一切精神创造的价值都是为了“明分使群”。当然,荀子当时讲的“群”,实质上是封建的宗法制和封建等级制度,荀子的目的仍然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进行辩护。杨朱的“为我”当然是片面的,荀子强调“群”是为封建等级制度辩护,也是片面的。
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就会发展为杨朱的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同样,强化群体利益也会走向虚无主义的道路,进而漠视和束缚个性,最终也会背离人道原则。在儒墨激烈的批判中,道家从杨朱的“为我”、“贵己”说走向庄子的“无我”、“无己”说。后来,正统理学家接过庄子“无我”口号,进一步强化群体意识,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灭人欲”就要“无我”,“存天理”就是大公而无私。这些背离都是人类认识发展的必经阶段,问题的提出比问题本身显得更重要,对问题的争论会不断地启发人们寻找到合理的答案,先秦诸子各家在个人与群体关系上的争论不断引导继承者去探讨。后来,王夫之说:“我者德之主,性情之所持也。”顾炎武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可以看出,在明清这些大思想家那里,个性原则和爱国主义精神开始统一起来,群和己是统一的。这也是中国古代哲学群己关系的主流。
中国古代哲学总的趋势是自然原则和人道原则的辩证结合、个性原则和群体原则的相互统一,这些价值原则和价值体系则是维系中华文化的根脉所在,它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这些价值原则和价值体系始于先秦,特定社会环境为激烈论争提供了必要条件。因此,先秦诸子在价值问题上的论争对中国传统文化起着奠基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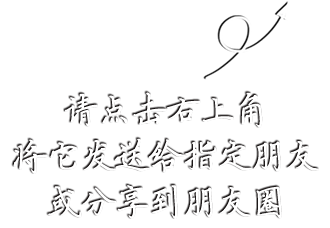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