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现代学者型女作家袁昌英的文学创作
2010年11月16日 13:53 作者:论文网论文摘要: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的、为数不多的著名女性学者,袁昌英的学术背景和学者气质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使她在中国现代女性书写里程中展现一种别样的风采。她在戏剧创作中自觉地运用现代西方艺术创作方法表现女性生命体验,取得了较大成功;在散文创作中,她在表现女性独特和细腻的感受时,也呈现出一种智慧和从容的学者气度。
论文关键词:袁昌英;学者型作家;现代意识;女性智慧
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中,袁昌英的名气显然不如后来的庐隐、丁玲、张爱玲等才女型作家,但是她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的女性作家之一,其开创之功是不可忽视的。同时作为中国现代最早的、为数不多的著名女性学者,她的学术背景和学者气质深刻地影响了她的文学创作,使她在中国现代女性书写里程中展现一种不同于诸多才女型作家的别样风采。
袁昌英于1894年l0月出生于湖南醴陵的一个官僚家庭,家境殷实,且接受了良好的日式教育,对中国古典文化有着扎实的基础。后来,她出国留学,曾先后去英国、法国学习文学与艺术。归国后,一直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等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在武汉大学时,与苏雪林、凌叔华交往甚密,相互砥砺切磋,时有“珞珈三杰”之誉。在其学术生涯中,她有着丰硕的成果,出版过《法兰西文学》、<西洋音乐史》等专著,在对西方文化的传播与研究上发挥过重要的作用,是一名学养深厚的知名的外国文学和艺术研究专家。这种完整的求学经历和学者身份在现代女性作家中是很少见的。这种专业兴趣和研究也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首先表现在袁昌英在戏剧和小说的创作中对于现代西方艺术创作方法的自觉运用。其代表作三幕剧<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就是一个非常鲜明的例子。“五四”时期,以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为题材创作的作品很多。王瑶先生也曾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他说:“譬如<孔雀东南飞>的故事里,是封建社会里为了婚姻不自由而牺牲的典型事例,在反封建战斗中,自然容易引起人的联想。以这故事为题材的剧本就有熊佛西的<兰芝与仲卿>,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四年级学生合编的<孔雀东南飞>和杨荫深的<磐石和莆苇》”但在众多的改写再造之作中,最为成功,也“最有价值、技巧也最为圆熟的压轴之作”,当属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
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文学中著名的叙事诗,诗歌叙写焦仲卿与妻子刘兰芝情深意笃,但因婆婆焦母家长制的作梗,而导致夫妻二人双双赴死的悲剧。“五四”时期,反对封建礼教、追求个性自由是时代至上的价值追求,对其进行新的叙写与表现无疑是切合时代的脉动。但在众多的改造之作中,人们要么直接高扬反封建主题,要么将兰芝与婆婆之间的矛盾转化为贫富冲突。这些改造的确是切合了时代主潮,也的确在历史人物的“骸骨”里吹进了“五四”精神,“借着古人来说自己的话”。但大都没有真正将时代精神有机地融人到戏剧艺术之中,在功利理性的先见中偏离了艺术逻辑。而袁昌英的改造则另辟蹊径,真正深入地把握了人物的内在心灵,也真正体现了戏剧艺术的审美魅力。
袁昌英留学国外时,便着力于研究西洋戏剧,发表了许多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有着相当高的西方戏剧造诣。也正因为具备这样的精深的学术背景,熟谙现代西方艺术创作方法,所以她在对《孔雀东南飞》这一旧题材的处理上,并没有简单地将戏剧冲突建构在封建家长与子女的对立与冲突上,而是从文化——心理切人,在人物生存的具体环境与客观现实中,以“人性’:为核心,从精神分析、家庭伦理和个性意识等多个层次去构造,让戏剧冲突既有着现实生活的骨骼,更有着个性心理与精神的肌质。特别与众不同的是她还加深与强化了焦母这个形象的分量,而且这一形象俨然成为了戏剧的主要人物形象。在汉乐府民歌中,诗歌核心在于表现兰芝的勤劳善良、对丈夫的深情厚意、对爱情的坚贞、对命运的抗争。而在袁昌英的戏剧中,作品却着重于表现焦母的复杂性格与深度心理,焦母成了戏剧冲突的纽结,是整个作品的关键所在。在袁剧中,焦母三十六七岁,固执倔强。丈夫早死,她独立支撑,含辛茹苦地把仲卿养育成人。作为一个不幸的女性,儿子不仅成了来日生活的依靠,而且成了她“精神上的情人”和“心理上的伴侣”。其舐犊之情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恋子之情”。这种“恋子之情”内在地潜藏着对“丈夫”缺席的补偿,是精神心理的一种变异的满足,但伦理律令让这种心理被强制地压抑,最终也就成为一种盲动的无意识,对于一切外在的“威胁”有着极为强大的反拨。“谁敢来夺我的儿子去……任谁来,我都得和他拼命。”正是因为对母子情感的过度依赖,焦母的情感日益变得病态,对儿子的爱不再是一种真正的本质性的爱,而变成了一种对对象的占有。同时,这种变态的情感让她的心理承受能力变得异常脆弱。如果说,在儿子未曾结婚时,对儿子的依赖与占有不必有所担心,失去儿子的危险只是一种潜在的忧虑的话,那么,刘兰芝的出现则让这种失去儿子的危险成了一种现实。于是,先前因生理与心理积蓄的盲动且充满敌对性质的力量在具体“敌人”那里被激活,兰芝也就成了尽力发泄的对象。于是,她处处与兰芝为难,对其实施打击折磨、进行心理与生理的双重虐待。并且在这样的一种变态的宣泄中,扮演着“虐待狂”的角色,并获得一种病态的“快乐”,也就是焦母所说的“难道只有我苦得,别人苦不得吗?”。但是,作者并没有将焦母的这种状态仅仅归结为一种病例,而是将其放置在封建伦理文化中去表现的。话剧中与焦母年龄相当的姥姥就直接道出了封建贞节观念压抑与戕害下女性的沉重的悲苦与辛酸,“我倒吞下去的眼泪倾出来,怕不难浸没村口那座牌坊哩”。也就是说,正是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与压迫让女性承受了过多的委屈与辛酸。焦母的悲剧与其说是精神与心理的悲剧,还不如说是封建伦理一手造成的性格与命运的悲剧,正是袁昌英赋予它以丰富深厚的心理内涵,在文化的与心理的两相结合中,让作品具有了厚实的底子,也更具有扣人心弦的艺术张力。因此,从《孔雀东南飞》的改编上,无论主题的切人还是焦母形象的塑造上,我们明显的可以看到袁昌英对西方文艺观念的借鉴和吸收,也正是这种深厚的西方文艺素养帮助她取得了《孔雀东南飞》的改编的成功,甚至奠定了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尤其是戏剧史上的地位。
上世纪30年代,是时代书写转向革命话语的时代。学者的求真态度使得袁昌英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的创作立场,不趋从时世,坚持从自我的视角去揭示生活中的矛盾与冲突,在学者式的理性思考下,表达现代女性本真的生命体验。而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她写出了许多不同于主流话语的问题剧,在剧中塑造了许多鲜明的女性形象。 如在《究竟谁是扫帚星》中,袁昌英着力塑造现代知识女性的形象。玉芳作为一个“二十世纪的新女子”,有着较为激进的个性意识,大胆地宣称“我应当从底上铲除那些陈旧的观念,过我自己要过的生活”。当她发现自己所倾心的惟我虚伪自私、多疑善妒时,并未犹豫不决,也不是如一般女性那样柔弱不舍,而是毅然地与他分手,“请自便吧,以后请永远回避我的视线。我们的一切都从此一刀两断,斩草除根了。”这里,我们不仅可以见到现代知识女性的独立意志和自由个性,而且也表现出作者对于自由婚姻的深入思考,自由爱情的获得并不仅仅是摒除来自封建家长的作梗,而且有来自爱的对象的种种缺陷和不足。《结婚前的一吻》中的李雅贞与玉芳相比,虽然缺乏现代知识女性的激进意识,但却具有传统女性温柔敦厚、明理大度的美质。她在爱情观念上有着保守的一面,与自己的未婚夫的订婚虽是遵父母之命,虽也觉得“遵父母之命不能如平常一样自由,然而却是灵体二者的完满结合”。但与许多只注重自我的利益,却不顾他人自由与尊严的女性形象不同,她将自我的道德建立在他我两利的基础之上的。但当知道自己的未婚夫所爱是自己的表妹时,便大大方方地退出了这个爱情场,而成就了孤女黎爱珍的幸福。她的行为可说是真正符合了鲁迅先生所说的“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可以说,这样一种戏剧结局从一定层面再次确证了自由恋爱的才真正体现现代爱情的本质。
其话剧《人之道》与上述肯定自由恋爱的主题有所不同,而是透过“自由恋爱”的时代主潮,理性地审视其中所隐藏的阴影与黑暗,揭露其中所掩盖的虚伪与丑陋,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那些自称新男女的人们假借自由恋爱为名而僭越道德与责任,自私地放纵个人欲望的丑恶嘴脸。勤劳善良的王妈在出嫁后为支持丈夫出国深造,自己一人独立担当起抚养子女支撑家庭的重任。始料未及的是,丈夫另有新欢,与她断绝夫妻情分。当她带着孩子去上海寻找久久不归的丈夫时,却发现自己帮佣的男主人竟然是自己原来的丈夫。此时的他已经是另寻新欢.,重组家庭,对她的到来可说是凶相毕露。在儿子患病天亡,五内俱焚的情形下,她绝望地自绝于车轮之下。袁昌英为戏剧取名“人之道”,用《道德经》“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之意,尽管其批判往往显得有些肤浅,仅仅局限于道德批判,而无法从道德与历史的二律悖反中发掘更深的内涵。但这个作品显然不是一个单纯的婚姻问题剧,它的意义不仅仅体现在婚姻爱情领域,而是切人了袁昌英对“五四”个性解放与自由思潮的理性反思与审视。与上述关注爱情与婚姻问题不同,话剧《活诗人》、《文坛幻舞》则主要是探讨艺术与生活,文学的本质与意义的作品。《活诗人》中,美丽多才的少女李雪梅面对三位追求者无以取舍时,于是以谁作诗又快又好作为条件。当一个文学青年从恶狗口中救出小猫而耽误作诗时,获得了雪梅的欢心,因为“没有真挚的情感与高尚完美的人格,任他的诗写得如何天花乱坠,也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
《文坛幻舞》则主要是通过萼英反映了文坛中金钱对艺术的侵蚀,左右诗人人格导致堕落腐朽的悲剧。尽管这些作品多从自己的艺术情趣出发,反映小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片羽微澜,缺少应有的生活气息与艺术张力,但依然可以看到袁昌英对于生活学者式的理性关注。
散文在袁昌英的创作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由于出国留学和多处执教的经历,“从国内到国外,她纵横的足迹踏过了那么多地方”,因此在她的笔下出现了非常“丰富生动的事物”,从国内的名山大川到域外的小街村镇,从让庐中的人文趣事到战争时代的国事人生,种种广博的见闻,她都有所记叙,往往能够在文字之中寄寓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艺术才情,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然而,“她的散文又和我们常见的写景抒情、借物抒情的散文也不相同,袁昌英善于在散文中发表议论”。这在现代女性作家中是鲜有其匹的。
袁昌英为什么会写出大量周作人所说的“论文”呢?联系她的人生就不足为奇了。作为最早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中国学者、女子之一,又在国外生活过不短的时间,袁昌英对于西方社会和中国现实、对于女性生存和人生人性都有自己的看法,所以常借助“论文”来加以表达。同时,由于她熟谙西方文艺和哲学的学术背景,袁昌英受西方随笔的影响颇深,不仅喜好在文中发表议论,而且喜欢借助西方哲学与心理学知识来思考人生,阐述人生的感悟与体验。这使得她的散文,“就同我国传统的某些散文用自己的议论来证明‘圣人’的名言大不相同”,而散发出现代的气息。如在《行年四十》中,袁昌英就运用现代医学与心理学知识,来阐述中年女性身心的特殊变化,她写道:“四十是人生的最大的一个关键,在生理上说来,一个人由出生至四十是如东升的红日,一步步向着午天腾达的,只有越来越发扬,越来越光大,越来越辉煌的,可是过了四十,就如渐向西沉的黄金色的日轮一样,光芒也许特别的锐利,颜色也许异样的灿烂,热力也许特别的炽热,然而总不免朝着衰败消落的悲哀里进行;四十是生命向上的最后挣扎;尤其是女子,那天生的大生命力要在她的身上逞其最大的压迫,无上的威力,来执行它那创造新生命的使命。”不仅语言灵动,比喻新颖,传达了女性独特的和细腻的感受,而且充满了学者式的真知灼见,散发一种浓郁的现代意识。再如在《漫谈友谊》中,袁昌英也是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知识,论述心与心应当相通,因为人需要与他人发生情感联系,“这种要求,现代心理学称为爱群天性。”也可以明显感受作者的学者气质。
正是因为袁昌英是“以一个学者的头脑来写散文”,所以她的散文呈现了一种现代女性散文少有的智慧之美和学者气度。由于学者的理性思维的渗入,她的散文条分缕析,思路清楚,如《在法律上平等》对于女性遭遇不平等的现状的探讨,既枚举了“民国”后种种歧视女性的规定,又深入剖析了这种歧视的根源,说理透彻而明白,可贵的是还能够对女性自身的不足进行审视,显示了作为学者的理性。再如《关于(莎乐美)》,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于唯美主义的进行分析,逻辑严谨,有理有据,持论公允,也反映了作为西方文艺专家的袁昌英的辨识力。
袁昌英的散文的智慧之美和学者气度还表现在她喜欢旁征博引,充满了现代女性散文少有的“理趣”。由于作为学者的袁昌英具有渊博的知识,因此在发表议论时候,经常会引用不少的有趣的知识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使得她的许多议论性散文洋洋洒洒,从容阔大,同时以丰富的知识性给人以启迪。如《生死》,围绕着论点,袁昌英例举了古今中外众多的人物和文学形象来证明,周公、孔子、释迦牟尼、文天祥、岳飞、诸葛亮、史可法、王莽、袁世凯、贾宝玉、屈原、庄子、司马迁、杜甫、李煜、八大山人、王实甫、曹雪芹、华盛顿、林肯、贞德等,简直让人目不暇接,真是横贯中西,脚踏古今,任意纵横腾挪。袁昌英的这类散文创作在众多女性散文创作中别开生面。
总而言之,作为现代最早的女性作家之一,袁昌英不仅为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用她的文学实践确立了现代女性在这一领域的存在。而且也因其作为学者而兼创作,学术背景和学者气质对其创作的渗透,使她在现代女性作家星空中闪烁着别样的光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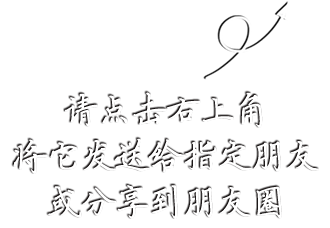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