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张承志“后《心灵史》”阶段创作中的几个主题
2010年12月06日 14:46 作者:职称论文论文网(www.lunww.com )是期刊推广、论文发表、论文写作指导的正规代理机构,我们与4、5百家省级、国家级、核心期刊有合作,我们合作的期刊都是万方、维普、中国知网、中国新闻出版总署收录的正规期刊。合作的期刊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可查,详情可来电0519-83865052,或者QQ:85782530咨询。
“后《心灵史》”阶段不是理论界的提法,而是张承志在1993年对他本人创作的一种期望性描述:“在我的所谓“后(心灵史》’阶段。我盼我的文学有独立的思想和新鲜的文风”((清洁的精神·后记》)。从时限上说,“后(心灵史)”阶段是指1991年(心灵史》完成以后至今;从形式看,此一阶段中止了小说创作,致力于散文及学术文章的写作。张承志认为,作为虚构和想象性艺术的小说,在传达思想方面是远远不及散文的,而散文也能够更好地表现真实。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他再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弃迁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人心所欲的散文之中’((新集编后》,载(文艺报》2的1年4月17日)。在‘卜后《心灵史》”阶段,张承志思考了许多重大的文化命题,如时代、国家、民族、宗教以及正义、人道、美等等,体现了他这一时期创作特点的主题。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i.民间世界;2.反智论(即对知识分子的批判);3.文明代言人理论的提出。需要指出:对上述主题的描写和议论.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批判以及为之寻求参照的思维模式。也就是说,张承志所关注的,仍然是中国文化的现状和发展。
一、民间世界
从1984年始.张承志有意识、系列性地描写他自称的“文学上的三块大陆”,即:蒙古草原(文化)、新班天山枢纽、回民的黄土高原。在迄今为止已出版的7本散文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鞍与笔》、(牧人笔记》、《以笔为旗》、《一册山河》)中。张承志不厌重复地描写了这三块大陆历史和现实中的地貌、风土、民情以及许许多多的小人物,并以文学化的方式具体考证研究了“比如关于蒙古游牧民族与马、蒙古民歌的性质、突厥与中亚、回教苏非主义”等艺术意味很浓的命题((荒芜英雄路·作者自白》〕。可以说。这已构成了一个文学和学术的基本民间世界。虽然从文化中心或主流文化视角看.这些作为文化文本的民间世界向来处于弱势和边缘地位,但是它们自身所拥有的那种底层的系统价值观念,特别是关乎人心、人道或信抑的价值观,确实有着一种别样的生命力或魅力,而这正是张承志所要发现和披露的。他的目的是明确的:……从骨头到语言,我紧紧攀援日夜吮吸的,是另一种强大的、未被认知的、底层民众的价值观点和文化体系。……不仅如此,我还奢望着这‘另一种’有一天会在源头上与中华文明的‘这一种’清澈合流.给垂老的文明以接济……’((折一根发发草做笔))因此,描述’‘文学上的三块大陆’,以此为中国文化提供一种参照、建议和补充。是张承志’‘后(心灵史》”阶段主要的创作思路,通俗地说,这种参照、建议和补充所提示的相关内容及其精神,在张承志看来,是中国文化所缺乏或没有的。
通过对中国文化的考察,张承志得出了如下批判性的结论:‘’这个文化从古代起。渐渐发达成熟为一种能与一切宗教文化匹敌的文明。它广大精深.丰富美好,但是它偏重着世俗的精神,它培育着一种绝对的拜物论.以及彻底的实用主义’((在中国信抑》。张承志不止一次地表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且也明确地陈述了自己是中国文化养成的作家((无援的思想》,他希望个人所属的中华文明有.‘华美的色彩”《正午的喀什》,在这样的前提下,张承志分析并标示出中国文化中的两个缺陷和弊端:一方面,它很少有对信仰的执著精神,并缺乏对人心、人性的终极意义上的关怀;另一方面,世俗精神运作于当前现实生活及文化心理中,滋生出了诸如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等等现象或思潮.这是中国文化自身产生出的副产品,反过来又可能侵蚀文化母体本身,这种观点已经得到了一些回应或赞同。青年学者王彬彬在一篇文章中的论述,我以为是对张承志此类观点的最好注解:“……市侩主义,实用主义.拜金主义,甚嚣尘上.工具理性恶性膨胀。侵占着价值理想的家园……”(见(独白与驳洁)一书)。
而“文学上的三块大陆”所具备的那种未被发现和认知的底层价值观.在自己的世界中.外现为一种“丰满的文化和人的生活’((正午的喀什》},这就是张承志为什么反复描述新疆文化枢纽中的美丽、回民黄土高原中的信抑、蒙古草原文化中的自由等等诸如此类子题的缘故。比如新疆文明和文化中,有一种’‘柔和了、变成了艺术的仪礼的力量“。有一种“变成了传统文化和气质以后的信仰的魅力”,因为“在这里,宗教成熟了,变成了和谐的文化。简洁的圣行,化人了每天的生计和日常的习惯。渗进了音乐和体质。变成了姑娘和男子头上的花帽.演化成饭前的洗手和饭后的感恩。这样的文明魅力十足,每一个儿童都在它的哺育中长大,每一个姑娘都觉得这样更美,甚至每一件坏事。都在它规定的限界到头和终《正午的喀什》。凡在描写三块大陆的一些重要细节时,张承志都会自然地联想到中国文化,如黄土高原大山村落中的“让路”这一礼貌行为,他写道:“‘让路’—在中文中尽管还有这个词汇存在,但除了在这片黄土世界里,你在哪里也难找到这个词汇产生时的古老景象了”《回民的黄土高原》)。此种体现为“丰满的文化和人的生活”的底层民间价值观,应该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参照、建议和补充,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在“人们为种种同题苦恼的今天”,这是“一把能解开你的苦恼的钥匙’《回民的黄土高原》。
“参照’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或在何种条件下方能发挥其功能,这必然遇到一个交流和对话的障碍,即:中国文化虽然滋生着诸种弊端,但它本身所具有的那种强大的优势,能否对边缘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可视可见呢?我想,张承志对此有着清醒的头脑,基于以下的认识,‘’参照’有可能以某种形式进行,即:在心灵关怀上、在符合人性的生活方式上、在对信仰的执著上,等等,最发达丰富的文化所缺乏的,正可能存在于底层的民间文化世界中,这应成为一种参照的必要条件;其次,“参照’‘并非照擞,比如,张承志对回族伊斯兰文化中有关信仰的论述,目的并不是在于要求原样照搬,而是从信仰所具有的那种执著精神中获得关于人心‘人性的某种启示,由此使文化成为符合人的生活的合理形式,也即构成为一种“丰满的文化和人的生活”。
除上述“参照”意义外,张承志在描述他如此挚爱的民间世界时,并没有将其价值观完美化、理想化,也没有将其中的民众神圣化、崇高化,他也时刻留意且警惕着其间可能存在的非人性的因素。比如对地位更低或弱者的歧视,因为歧视是“人类最卑鄙的本性之一”。在这方面,张承志的态度是明确的、决绝的,他有一篇回忆50年代内蒙插队时外人打狗欺主的散文,其中写道:“有朝一日,恻若她(即额吉)的后代远离了那种立场和地位,或者说俏若他们也朝着更低贱‘更穷的人举起马棒的时候—我和他们之间的一切就将断绝干净‘’((狗的雕像的联想》}。在描述“文学上的三块大陆’‘的作品中,关于回族或伊斯兰文化的散文数量是最多的,他对这一个个人认为是真正“民间’〔《刘介廉的五更月》)的世界及人群注人了热烈的情感,但是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忘记投以警觉和鉴别的眼光:“当身处在穆斯林之中或生活在他们的聚居区时,我留意是否发生过我们对更弱小者的歧视”(《人道和文化的参照))。
尽管张承志用了异质文化的术语来形容“文学上的三块大陆”,但在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方面,它们体现出的是异质同构的特点,即在中国文化这个大的系统中,它们是子系统,是不可分的组成部分,虽然历来处于极边缘的地位。这是张承志文化(文学)思想的主基调,是不应被忽视的。
二、反智论
张承志对当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最早可上溯至1984年,这一年他公开宣布了与“文人的团伙”的距离,并开始了自己沉人民间世界及与民众结合的实践道路(《离别西海固》}。在’‘后《心灵史》”阶段,对知识分子的自觉性批判成为他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这亦可称之为“反智论”。张承志的“反智论’。一方面有其承传或思想资源,即鲁迅传统,他的主基调甚至某些术语都直接源自于鲁迅.如“智识阶级”、“伪士’等。另一方面,也有其当代性因素,即对当代知识分子地位的批判性考察。在张承志看来,当代知识分子不能只满足于熟练或精通一门学术,而且也要在这种学术事业或学术活动中,能够体现出正义、良知或“布衣之士的精神’(《再致先生》);在更高层面上,达到王阳明“知行合一”所要求的境界。张承志曾谈到了一部分日本作家,这些作家身上所体现出的“知行一致的精神’,令他叹服;尤其在日本的一些女作家身上所表现出的醒目的“正义之利器”的精神。更令他喜欢(《人道和文化的参照》)。但是,如果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仅仅以熟知一门学术为其终极目的,‘’敬学间远大义”,且在文化上营造出那种人所难以凭知识与之抗衡的’‘透明温和的场道’,将其置于思想史的意义上衡量,则不过是如鲁迅所说的“伪士’而已。
将张承志对知识分子的价值定位抽绎出来.有如下两点:首先,“知识分子始终对社会和权力保持基本的批判火力(《再致先生》)是其主要的责任,由此确立自身在当代社会及文化生活中的地位,这实际上更接近陈思和先生所说的知识分子的“岗位职责”(见(新文学传统与当代立场》一书),因为对自己从事事业的执著信仰,以及强烈的个性和对社会的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正是知识分子的地位和文化身份的标志;其次,在与民众的关系上,傲到对民众生活及其心情的了解和尊重,更进一步在心理世界上认同于民众或者成为其中的一员,使自己有一种“布衣之士的精神”或‘’正义和朴素的平民精神’(《都市的表情》)。
因此,知识分子的地位以及与民众的关系就成了张承志考察和批判当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基点。也就是说,张承志并不是抽象地或不加区别地批判、否定,而是一种鉴别性的批判,比如他曾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典故,来鉴别并泛论当代一些知识分子在自身地位上的偏离,‘’毛’即知识分子总是想脱离“皮’(即民众),“想背叛皮并扔了它”(《日文(鞍与笔)前言自译》);再如具体的、分类性地对真伪作家的鉴别,真的作家在创作实践中采取一种“言行间的约束自警”.也即言行一致。并体现出一种正义、良知的精神;伪作家则在心与言、言与行之间缺乏一种恒定一致的关系,也即“无行’(《无援的思想》)。他特意对比性地提到了’‘伪作家”和“伪作品”的干扰:“·一由于伪作家和伪作品的干扰,人们浪费了多少精力呐。今天,真诚而正义的文学陷人了孤独冷清,这是最最好的事情”(《荒芜英雄路、后记》)。因为在最终的意义上,真正的文学和“作家的成色”要经受历史老人的严格审视,“文学的圣殿里,就终极意味而言,容不得作家的一点作伪”(《人道和文化的参照》)。在鉴别过程中,张承志对知识分子中的作家和民族学家这两类人的同一种行为,给予了比较激烈的批评。首先是作家的“采风”活动,这种活动,在表面上也是一种接近民众生活的方式,但在张承志看来,剥开其内里,这实际上是对民众情忿更深的伤害,因为这种方式中“没有端庄的举意,缺乏儿子或战士的热烈感情”,只有猎奇心态,所以,他对“采风捞故事的文人行径”表示了“鄙视”(}-册山河》);其次,对一些民族学家的学术活动提出了质疑;“会说老百性的语言吗?会说民族语言或者方言么?多少知道这一方水士的来龙去脉么?能够听到当地的苦楚和感到世间的不平么?”(《一册山河》)因为现实中更多见的是,比如,一个人从未涉足过内蒙古草原牧区,但是他借助于大学、研究院、现成资料,甚至出国留洋就可以成为一名蒙古学的专家,可这与活的民族的生活史和情感史有什么关系?张承志认为,这些学者们的“高深学术对日常生活的无知比比皆是”((从象牙塔到吐鲁番》),或者仅限于“残卖中国的民俗画’,这都是因为“缺乏对民众的感悟和歌重”〔《心灵模式》)。
上述表明,张承志的反智论既非反对知识本身,也不是反对或否定全部的知识分子,他自己曾表述过,“我并不是一个不剩地敌视知识分子,我只是抗议流行中国的某种思潮’(《墨浓时惊无语));他所反对或批判的,也仅是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而且保持着他个人的一种基本的批判底线。王彬彬对此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道:“1··…张承志的‘反智论’反的是‘知识分子’中的‘分子’,并不反智性、知识。·一张承志充其量只能算是‘反知识分子’。而且,张承志的矛头也仅仅只指向同时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张承志对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其实也令我想到鲁迅。对同时代‘知识分子’,鲁迅也是从不掩饰自己的蔑视和僧恶的,‘学者’、‘教授’、‘智识阶级’这类称号在鲁迅笔下出现时,往往都带有讥嘲、消汕的意味。但鲁迅却从未表现出对智性和知识文化本身的不屑和娜视。一在这个问题上,张承志更多地表现出与鲁迅相近’((独白与驳洁》)的一面。 张承志对知识分子尤其文人、学者的批评是激烈而尖刻的,恰像鲁迅一样,他在文章中不放过任何一次可能批判的机会‘至于诸如“酸文人”、“四眼兄”,‘’写得纸腐墨臭的文人”等名词,我们能够在他的文章中信手拈来。张承志的态度如此激烈,这实际上与知识分子在当下现实中的行为,确切地说在金钱与权力面前的表现有关,“中国文化面临的危机,以及知识分子在权力和金钱面前的作为,会使我的思想依然激烈”,但张承志也表示,对这方面的批判、自己要“警惕偏激”((首届“爱文文学奖”受奖致辞))。张承志也从正面呼吁了“一种不同的知识分子的出现”((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其含义应有两层:真的知识分子不但具有真正独立自由的个体精神,也能够以平等或尊重的态度对待民众;另一层意思是,在民间世界,比如内蒙古草原出现本民族的知识分子,“一定将挟裹着风雪的寒气,携带着羊皮的温暖、遵循着四季的周始和五畜的规律、以全套的牧人话语描写出来”(《折一根龙贫草做笔》)。同时,他也从正面对真正的作家作了描述:“真正的作家,必须具备良知和艺术,必须拥有独立的知识分子立场与气质,包括高贵的行为方式”〔《人道和文化和参照))。
三、文明发言人理论的提出
所谓文明发言人理论,即“发言者资格的问题,关于文化的声音和主人的间题’(《二十八年的额吉)),是张承志在民间世界长期实践、思考以及他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和知识分子定位的初步结果。这个理论依然是基于对作家或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的思考。
张承志很早提出了一个方法,即“正确的研究方法存在于被研究者的形式之中”,要“忠于民众的心”(见(心灵史))。在“后(心灵史》”阶段,张承志多次强调了“民众的心情”、“心情的真实”。在他看来,这应该成为作家或知识分子在创作中面对民众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因为,一般而言,比如作家在描写民众的生活时,是以个人既成的价值系统来审视、来取舍,他首先考虑的是个人价值和审美的完整性,而不是被描写对象的完整性。比较理想的结果是,他可能表述出了民众部分真实的生活及心情;较坏的结果是,对民众生活和心情进行了某种切刹,出现在他作品中的民众形象及其生活史、情感史,很难保证不被变形或歪曲,借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话来说,这便成了“文学中的谎言”〔(番石榴职香》)。因此,张承志提出“被研究对象的形式’以及要“忠于民众的心”,是以个人的经验在根本上为作家定位提供了某种参考。
内蒙古草原的义子、回民黄土高原的儿子、新级天山至死不渝的恋人,这是张承志对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定位(《语言值憬》)。199,年出版的图文集《大陆与情感)就是他与民众结合的一个动人例证。在本书前言中,他深情地写道:“用图片再次描述自己的文学安身立命的三块大陆—蒙古大草原、回民的黄土高原、文明的新,;表达这三块大陆的民众对自己的支撑、友谊与哺育;作家只是儿子,只是引线,图片中的三块大陆上的民众,才是主题和主人公”,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救过程,一个作家与民众结合的真实故事”,图片中的年代,从ma到1998橄跨30年,这也就是张承志自述的,“我用一生的感情和实践”‘为文明代言人理论,“为解决这个间题提供了参考”((二十八年的额吉))。1995年,张承志出任三联书店《人文地理》杂志(后停刊)执行主编,他写了一篇发刊辞,这就是著名的《人文地理概念之下的方法论思考》,这篇文章是他文学和学术思想的一个升华,也是他几十年来与民众真实结合的一个小结。在文中‘他从学理的角度论述了民众(文明主体、文明主人)和知识分子、作家(代言人)之间的关系,并试图解决他长期思考的有关文明代言人资格的理论问题,并以此来打破“书斋学术对文明主人的话语压迫”(《高贵的精神》)。他认为,文明主体就是’‘民间、民族、山野农村的文明主人和生活者’,在他们身上,事实上具备着一种被知识者所忽略或有意无视的特点,即:1.天下万民,生而知之;2.鲜活的民众生活中藏着正确的解释。但是,民众役有书写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还没有对文化的权利意识,更何况他们也羞于解释常识。而令人担优的现象则是,作为文明代言人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在面对民众时,很有可能“存在话语的塌道、文化的歧视和片面的胡说”。为校正这种现象.就应解决知识分子和作家与民众之间的“地位关系”。张承志数次陈述了民族学大师摩尔根曾被美洲原住民部落接纳为养子的历史事实,将之作为一种必要的“参照”,“必须指出。养子,这个概念的含义绝非仅仅是形式而已。这是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对自己地位的‘纠正’冲,所以他期盼在“摩尔根的意味深长的道路上’,有人能回到求知的本来意义上。这里已经包含了张承志对文明代言人在态度和方法上的初步理论构建:首先,知识分子和作家要“成为杜会和民众的真实成员,然后,再从社会和民众中获得真知灼见”,这是对基本态度的构想;其次,“就是学会和底层、和百姓、和谦恭抑或沉默的普通人对话”。这是对方法的构想。
“对话”这种方式所包含的意义是:它要求知识分子和作家与民众在各自的地位上处于平等状态,各自都有着主体性地位,都有着独立的意志、情感、价值等等,谁也不能否定、歧视对方;另一方面,因为民众一直处于底层、处于劣势,缺乏对文化或话语的权利意识。因此,在面对民众时,知识分子和作家要以求学者的态度。学会如何对话、如何倾听,因为只有在民众开口时‘而且“一旦他们开始了指教,求学者找到的,就可能是真知,是谜底,包括自己人生的激动”。
但是,代言的方式永远存在着危险。根据张承志对既成文化现象的现察性描述,一种对文明、对底层民众的语言畏害己经出现,这就是:“他们解释着概括着,要不就吸吮着榨取着沉歌的文明乳房,在发达的外界功成名就”(《二十八年的额吉》〕。即使在自以为理解和宽容地对待民众的代言人身上。就一定不存在无意中的歧视吗?在这一点上,张承志始终保持着替觉。甚至包括对他自己也是如此,比如,当有人赞誉他的草原小说写得怎样好时,他会产生某种不安的感觉;而对自己的学术著作,他也做着一些自检工作—“十数年来的写作生涯中,有时我觉得心头袭过一种不安。书生的行为,正与牧人相反。梦想世代留传‘总否认面临淘汰。我清楚自己身上发生的异化。因此,侮当体内残存的牧人感觉苏醒的时候,就感到犯忌的恐怖”((折一根发岌草做笔))。
文明代言人资格理论中。要求代言人有真真切切的“双足泥巴的地理体验”((水路越梅关))。这在目前恐怕还只是一种理想的勾画。张承志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没有放弃希望和努力:“无奈体验的件件事情,大多只是一些象征。我们不过想摸索—文明在危难时的姿态,不过想寻找—第三世界的、高贵的文化表达方式。虽然它只像一丝沙澳中的声音,掠耳消逝了—它曾带着我们,向着一种人的理想跋涉过。何况还有具体的努力,它们也并非那么不具意味—我们对自己设定了的原则.实行了知识分子的自律。二我们在探究文明的俐释权,在尽力学习多种专业知识。目的是一种吃语么‘我们企图打破—书斋学术对文明主人的话语压迫。如同一群步行的堂吉诃德,虽然连皮马和名号也都没有。赤着手,块乏一支锈矛,但我们幻想着大战风车’(《高贵的精神》)。
上述三个主题是相互关联的。能够基本反映出张承志“后《心灵史》”阶段的创作趋向及特点。张承志是站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五四新文化(文学)传统的基点上,来描述比如三块大陆这样的民间世界的风貌及其精神等等,以之作为中国文化的参照.提供一种新鲜的血液。“参照’在另一个意义上是为沟通,“我的书写语言是汉语,我受到的是中国文化的启蒙和哺育。我幻想用这么一生去追逐一点沟通一‘’((人道和文化的参照》),无诊这种沟通取得了多大程度的效果.沟通本身就显示出了一种意义.包括对知识分子的批荆,以及文明代言人资格理论的提出。其目的皆是在于使他所属的中国文化(文明)增添一些华美的色彩,激活一些清洁的精神。另外。在对民间世界的人文关怀方面。那种倾向鲜明的反歧视主题,使得张承志的创作实践道路从始至终充满了一种人道主义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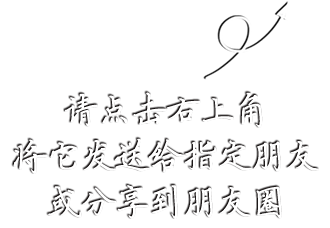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