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李贽的“童心说”和“化工说”
2011年3月07日 16:08 作者:论文网李贽是明代一位以狂放著称的思想家,公开以“异端”自居,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道学,注重个体生命之解脱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李贽重视作家主观情感的自然表现,强调情感之真诚无伪与表达之流畅通顺。于是他提出著名的“童心说”和“化工说”。
一、李贽的“童心说”理论
李贽的“童心说”是其文学理论批评的思想基础。就“童心说”来看,李贽围绕着“自然无伪”这个核心展开论述的。“童心”一词的本义是指人心之本然状态,即童稚之心,李贽认为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心之初也”。突出强调“真”,即人类童年的一种心理状态,它没有受到后天教化的影响。但李贽更看重的是表现思想情感之真诚无欺,这是与虚假伪饰相对立的层面。故日:“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即所言要发乎心,不要掩盖自我真实想法,要自然无伪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这是针对盛行一时的假道学所提出来的,李贽推崇做真人、说真话、做真事、写真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白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由此可以看出,决定作品价值的是“童心”,作者只有将“真心”融入创作中,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才有可能创作出来好的作品,这着重强调了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体作用。李贽更注重人格,他认为读古人诗文须注重作者投注其中的品格境界,真正能与古人心灵相通,方能有所收获。
但伟大的人格不是创作好作品的唯一条件,若想创作出不朽的文章还必须有才、有胆、有识。李贽本人狂放狷洁在明代可谓一流,论独立精神亦可谓一意孤行。他写文章随心所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却只能被视为杰出的文学思想家而非伟大作家。可见一位伟大的作家不仅要人格崇高,还应具备才、胆、识。以上条件具备以后,作者于临笔挥毫之际还需有“绝假纯真”之“童心”,只有如此,方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这个“童心”成了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于是《西厢记》、《水浒传》与《六经》、《语》、《孟》并列成为天下至文。这样,李贽在批判复古主义思潮的氛围里肯定了戏曲小说的文学地位,对后来的戏曲小说理论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水利论文发表二、李贽的“化工说”理论
李贽还提出“化工说”,他认为艺术造诣有“化工…画工”之分,“画工”是一种人为的极工尽巧,它虽能夺自然造化之细腻工巧,却无法与真自然相比,故李贽认为高明的《琵琶记》没有能深入表现人物真实自然的爱恋之情,而是极尽工巧地去刻画人物之全忠全孝,结果失去了感人的力量。所以真正的作品应如自然界的万物,有其自身的生存规律。李贽显然侧重表现作品人物之真实自然。故其“化工”乃指对客观对象的描述要达到逼真生动的程度,“画工”则指违背自然真实的人为加工。李贽所追求的“化工”即自然之美,它不囿于形迹法度,不在于字句、结构、对偶之间,也不在于道理、法度。李贽认为“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他们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是真性情的表现。
李贽关于化工与画工的理论无疑来源于绘画艺术,而且很有可能直接受到苏轼的影响。东坡论诗画肯定“天工”而否定“画工”,李贽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戏曲小说批评领域时,在保持其原有含义的同时,又拓展了其所含意蕴。如李贽评《水浒传》十三回日:“《水浒传》文字形容既妙,转换又神,如此回文字形容刻画周谨、杨志、索超处,已胜太史公一筹;至其转换到刘唐处来,真有出神入化手段,此岂人力可到?定是化工文字,可先天地始,后天地终也,不妄不妄。”此言化工乃取其自然不露雕琢痕迹的意思。小说叙刘唐至晁盖处送生辰纲消息,并不直叙,反远远由雷横巡乡入笔,化直接叙述为情节描写,在人物冲突中自然引出欲传消息,显得过接自然而无痕迹,所以称其为化工文字。又七十六回评日:“若欲借此阵法封侯拜将,待河之清也。”指其专注于细致描绘各种阵法,却毫无自然真实之感,是画工之作。这一用法与绘画中所用意义大体上是相同的。李贽还为此理论注入新的内涵,使之更适用于新的艺术领域。首先,从自然真实之内涵出发,强调作者在描绘人物时须合乎其本色如身份、口吻、性格等。《水浒传》四十四回杨林对石秀日:“四海之内,皆是兄弟,怎如此说?”李贽批日:“太文雅些。”(同回夹批)此言杨、石二人均为粗汉,如此说话不合他们的性格、身份。此种对人物本色的强调对于戏曲小说批评而言意义重大,这是因为只有将批评重点转向人物塑造成功与否,才算真正进入戏曲小说批评领域。李贽还认为小说欲达到“化工”效果,必须依据描写对象之情理,不允许作者率意而为。
其次,“化工说”又包含着传神的理论。李贽认为传神欲达到化工境界须具备以下两点:一是须真正将人物写活,达到只见其声音笑貌语言声口而完全忘记叙述之语言媒介。 水利论文发表
卓吾评《琵琶记》二十三出日:“曲与白竟至此乎!我不知其曲与白也,但见蔡公在床,五娘在侧,啼啼哭哭而已。神哉!技至此乎!”由此评论可知化工传神是李贽相当高的艺术要求。二是化工传神非但要准确描绘人物外在的语言行动,还需要重视人物内心世界之开掘。李贽评《水浒传》二十一回日:“此回文字逼真,化工肖物。摩写宋江、阎婆惜并阎婆处,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顾虎头、吴道子安得到此?至其中转换关目,恐施、罗二公亦不自料到此。余谓断有鬼神助之也”。此处透辟地论述了逼真、化工、传神三者间的关系,逼真即化工肖物,亦即如自然本身那般真实而无人工斧凿痕,且惟其如此方可称为传神。
再次,化工说强调戏曲小说之寄托寓意。卓吾论《拜月》《西厢》日:“余览斯记,想见其为人,当其时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间者,故借夫妇离合因缘以发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难得,羡张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叹今人之如土……小中见大,大中见小,举一毛端建宝王刹,坐微尘里转大法轮。此自至理,非干戏论。”(《焚书》卷三《杂说》)李贽依据自我认识去解读作品以寄托自身感慨,当然无可厚非。但我们必须承认他的“小中见大,大中见小”原则触及典型性问题,一个优秀的批评家理应努力揭示作品的真正内涵,这有益于对作品的理解和价值之判定。
中国古代戏曲小说成熟较晚,其批评理论也不发达,李贽率先将戏曲的人物、关目、情节作为其批评对象加以关注。将小说之形象塑造与情节安排加以重视,他的戏曲小说批评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理论初步建立起戏曲小说的批评模式,为后来的王骥德、李渔等戏曲理论家展开详加讨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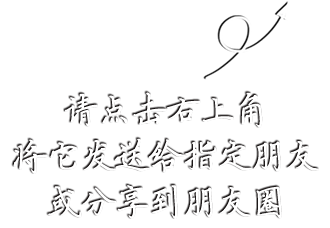
 发给朋友
发给朋友 分享到朋友圈
分享到朋友圈 回顶部
回顶部